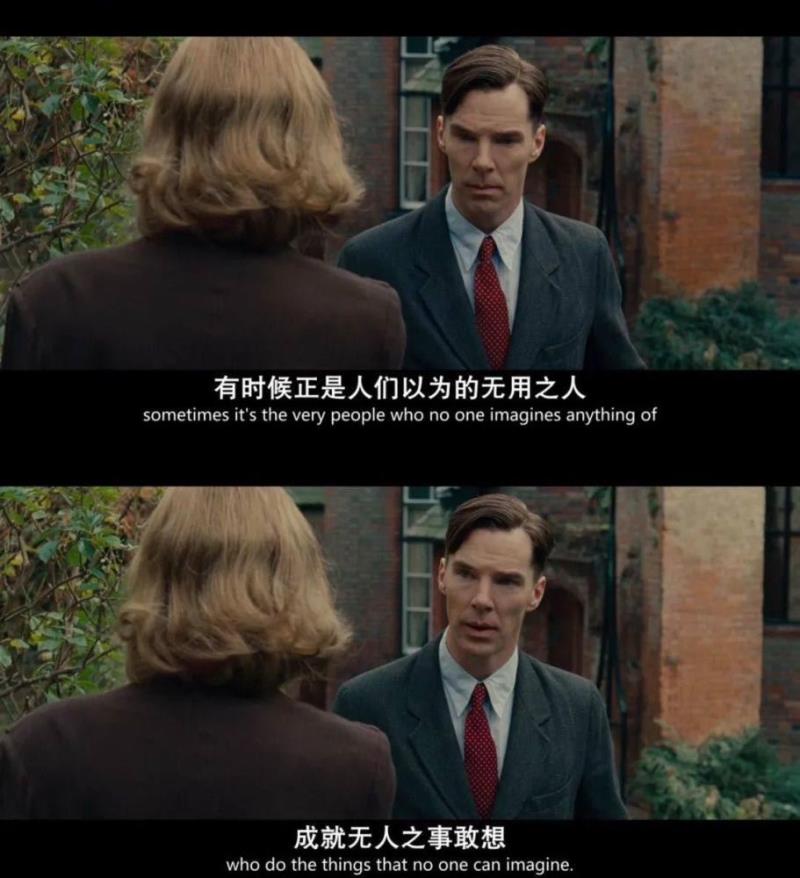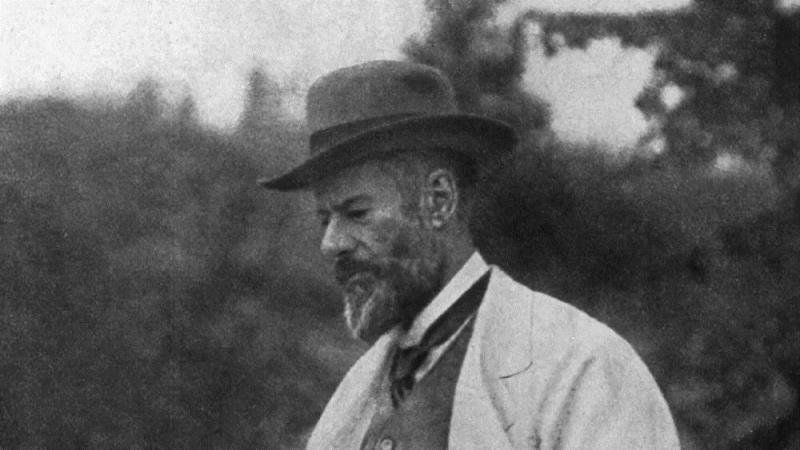?”
的確,在現(xiàn)代世界
,純粹的學(xué)術(shù)并不能帶來相較富足的生活,也很難再帶來顯赫的名望。
從去年的翟某“不知知網(wǎng)”卻獲得博士學(xué)位
,到今年仝某爆出“改身份”參加高考,再到前幾日博導(dǎo)之女“改成績保研”
,教育公平失衡
,學(xué)術(shù)之路也扭曲成了權(quán)力與地位角逐的工具。
那么
,今天學(xué)術(shù)的價值與意義何在
?
一百多年前,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德國慕尼黑大學(xué)為青年學(xué)生們作了《學(xué)術(shù)作為志業(yè)》的著名講演
。
這場演講以及不久之后的《政治作為志業(yè)》演講發(fā)生在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之下
。
那時候德國剛剛經(jīng)歷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敗,昨日世界已然崩塌
,新的社會及政治秩序尚未建立
,整個社會都處于一種動蕩的狀態(tài)。當(dāng)時的德國年輕人一方面在政治上相當(dāng)激進
,帶著一種左傾的浪漫主義
。
與此同時,他們之中也彌漫著一股迷惘的集體情緒
。
他們期盼著有人能告訴他們:今天的德國該怎么樣往下走
?年輕人應(yīng)該找到什么樣的人生使命?我們活著又是為了什么……
這是當(dāng)時年輕人的普遍困惑
。經(jīng)歷了一戰(zhàn)
,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開始對文明、對進步
、對理性都產(chǎn)生了巨大的懷疑
,渴求著意義與先知。
面對此
,韋伯登場了
。他并沒有給年輕人灌以“雞湯式”鼓勵,也沒有去滿足聽眾的期待
,發(fā)表對時局的洞察
。他反而以一種極為冷峻克制的態(tài)度,去回應(yīng)臺下熾熱的目光
。
他直白地說
,學(xué)術(shù)生涯是“一場瘋狂的冒險”
,工作投入很大但回報很少,作為謀生手段性價比實在太低
。
但是
,韋伯轉(zhuǎn)而說道,學(xué)術(shù)是值得作為精神上的志業(yè)
。作為“志業(yè)”
,即相當(dāng)于將個體的生命意義寄托于它之上。
可以說
,韋伯以極為審慎的態(tài)度回答了關(guān)于學(xué)術(shù)的意義
,這種審慎與冷峻其實正是基于他對當(dāng)時社會局勢的一種悲觀判斷。
他企盼引導(dǎo)人們走向清醒
,認(rèn)清現(xiàn)代世界的特征和自身的處境
;而與此同時,學(xué)會在良好的現(xiàn)實感中尋求有限的希望
。

作為人群焦點的韋伯
《學(xué)術(shù)作為志業(yè)》及《政治作為志業(yè)》這兩篇演說
,發(fā)表在韋伯生命最后的兩三年內(nèi)。1920年6月14日
,韋伯因感染當(dāng)時肆虐歐洲的西班牙流感
,引發(fā)肺炎去世,年僅56歲
。今年
,正是韋伯逝世一百周年的紀(jì)念年。
今天重讀韋伯
,具有特別的價值和意義
。你可能會發(fā)現(xiàn),百年之后
,我們所經(jīng)歷與面對的困擾和迷惘
,都未曾遠(yuǎn)離韋伯思想的范疇。
"
各種思潮和觀點
,彼此之間紛爭不休
,走向?qū)α⒎只诰裆舷萑肓藰O度的混亂
。
思想界彌漫著狂熱與騷動的情緒
,很容易讓煽動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他們編織迷人的幻覺
,散布言之鑿鑿的錯誤答案
,鼓吹虛妄的信心,誤導(dǎo)人們?nèi)で筇摷俚南M?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走向極端狂熱
;或者傳播貌似深刻的虛無主義
,讓年輕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悲觀和絕望。
韋伯決意要做一名抵擋者
,抵御這些迷惑對思想的腐蝕
。
"
祛魅時代的學(xué)術(shù)與政治
文 | 劉擎
(節(jié)選自理想國出版《學(xué)術(shù)與政治》)
1917年11月7日,在德國慕尼黑市的斯坦尼克藝術(shù)廳(Kunstsaal Steinicke)舉辦過一次演講
,主題為“學(xué)術(shù)作為志業(yè)”
。聽眾席擠滿了年輕的大學(xué)生,還有不少著名的學(xué)者
,因為主講人是當(dāng)時德國負(fù)有盛名的思想家馬克斯·韋伯
。
一年多之后,韋伯在同一個地方又做了一場演講
,題為“政治作為志業(yè)”。這兩篇演講后來結(jié)集出版
,被稱為韋伯的“志業(yè)演講”
,成為二十世紀(jì)西方著名的思想文獻,獲得了經(jīng)典地位
。
1.
祛魅的“夢醒時分”,
也讓人在精神上“格外荒涼”
韋伯的學(xué)術(shù)貢獻豐富而卓越,其中對現(xiàn)代世界特征的洞察尤為重要
。在《學(xué)術(shù)作為志業(yè)》的演講中
,有一個被廣泛引用的著名段落: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理性化、理知化
,尤其是將世界之迷魅加以袪除的時代;我們這個時代的宿命
,便是一切終極而最崇高的價值
,已自公共領(lǐng)域( ffentlichkeit)隱沒?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strong>
在這里
,“世界被祛除了迷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極為凝練地表達了韋伯對現(xiàn)代社會的根本判斷
,也是影響深遠(yuǎn)的一個見解
。
但“世界的除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用簡單的比喻可以這樣說:現(xiàn)代的來臨意味著一種覺醒
,像是世界到了“夢醒時分”
,解除了古代迷夢一般的魅力或者魅惑。
在現(xiàn)代之前
,人們生活在一個魅惑的世界中
,相信其中有神存在
,有精靈和鬼怪出沒,靈性不只限于人類
,動物也有靈性
,甚至萬物有靈。這些超越人類經(jīng)驗感知的所謂“超驗”的存在
,是冥冥之中難以言說的事物
,卻構(gòu)成了古代精神極為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
,古代世界籠罩在神秘的精神之中
,讓人難以理解,無法參透
,也因此讓人敬仰和畏懼
。恰恰是這種神秘精神,將人類與整個宇宙連成一體
,并從這種聯(lián)系中獲得生存的意義
。
古代人的終極價值,生命的根本意義
,不是人類自足的
,而是依托于比人類更高的存在,依賴于宇宙的整體秩序
。人們往往通過宗教信仰和儀式
,通過與超驗存在的聯(lián)系,確立生命的意義與目的
,獲得所謂“安身立命”的根基
。
后來,西方歷史進入了現(xiàn)代
。經(jīng)過宗教改革
、啟蒙運動和科學(xué)革命之后,西方人越來越傾向于以理性化的方式來探索世界和自己
,也就是說
,越來越信奉科學(xué)的認(rèn)識模式。
科學(xué)是理知化活動的典型體現(xiàn)
,依靠冷靜的觀察
、可靠的證據(jù)、嚴(yán)謹(jǐn)?shù)倪壿嫼颓逦恼撟C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茖W(xué)論述的特點是可觀察、可檢驗、可質(zhì)疑
、可反駁
、可修正,在根本上抵制神秘
、反對迷信
。
在這種理性化和理知化的時代,人們很難再輕信古代的玄思妙想
,不再接受各種“神神道道”的話語
。世界被理知化了,也就是被人看透了
。
比如
,在漫長的古代歷史上,日食或月食曾被視為神秘的天象
,而當(dāng)現(xiàn)代天文學(xué)揭穿其中奧秘
,這些以往“神秘”的天象變得清澈而簡單,一下子就失去了迷魅之處
。
世界被看透了
,沒有什么不可思議的說不清道不明的神秘之處。人們相信
,即有些事情一時還看不透,但在原則上終究是能被看透的
,其中的奧秘遲早會被破解
。
韋伯告訴我們,隨著現(xiàn)代的來臨
,一場精神的巨變發(fā)生了:古代世界那種迷霧一般的魅惑
,在現(xiàn)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驅(qū)散了。
現(xiàn)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時候
,會有一種“大夢初醒”的感覺
,這就是所謂“世界的除魅”。需要注意的是
,“世界的除魅”是對客觀事實的描述
,并不帶有價值判斷的傾向。
韋伯并沒有說這一轉(zhuǎn)變是值得慶幸的
,也無意去贊頌除魅之后的世界
。實際上,韋伯對此懷有復(fù)雜曖昧的態(tài)度
。
因為他知道,這個“夢醒時分”對許多人來說在精神上是格外“荒涼”的,信仰失去了以往神秘的根基,而科學(xué)又無法為生命的意義提供新的根本依據(jù),終極價值不再具有客觀性和公共性,會讓人茫然若失。
因此
,“一切終極而最崇高的價值
,已自公共領(lǐng)域隱沒”。然而
,世界的除魅是現(xiàn)代世界的真相
。
韋伯主張,無論對此感到多么無助多么失落
,我們必須直面這個真相
,這就是所謂現(xiàn)代性的境況。
在這種條件下
,學(xué)術(shù)生涯以及政治事業(yè)
,到底還有什么價值,我們?nèi)绾螐氖聦W(xué)術(shù)和政治
,都變成了極具挑戰(zhàn)性的困難問題
。
2.
等不過去的黑夜,
去與狂熱和絕望兩面作戰(zhàn)
古今中外許多為人傳誦的演講辭大多具有激蕩人心的力量
。而韋伯的這兩篇演講則相當(dāng)不同
,沒有去激發(fā)共鳴、感染聽眾
,反倒是刻意回避聽眾的期待
,抑制他們的激情。
因此
,這兩篇演講都有一種格外冷峻的風(fēng)格
。領(lǐng)悟這種冷峻的基調(diào),是解讀韋伯思想氣質(zhì)的入門鑰匙
。
如果我們仔細(xì)閱讀文本
,會發(fā)現(xiàn)兩篇演講的開場與結(jié)尾都是精心布局的,它們的開頭有明顯的相似之處
。在《學(xué)術(shù)作為志業(yè)》的開篇
,韋伯說他習(xí)慣用一種
“學(xué)究氣”的方式來處理問題。
對于學(xué)術(shù)究竟有什么意義
,學(xué)者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他沒有直接告訴聽眾所期待的答案,而是要用一種迂回的
、有點學(xué)究氣的方式
,慢慢進入主題。
類似的,在《政治作為志業(yè)》的演講中
,他開場的第一句就說
,
“在好幾個方面必定會使各位失望”。這里“失望”這個詞對應(yīng)的德文單詞“enttauschen”意思有點復(fù)雜
,同時有“失望”“幻滅”和“挫折”的意思
。
韋伯知道,聽眾非常期待他能對當(dāng)時緊迫的政治現(xiàn)實發(fā)表明確的見解
,但他從一開始就坦言
,他不準(zhǔn)備去滿足這種的期待,相反
,他可能會讓大家感到挫折和失望
。
那么,韋伯為什么拒絕迎合聽眾的期待
?為什么要故意采用帶有“間離效應(yīng)”的修辭策略
?在我看來,這是源自他對當(dāng)時歷史背景和德國局勢的洞察和憂慮
。
韋伯所處的時代
,見證了德國的巨大變遷。二十世紀(jì)初
,德國經(jīng)濟迅速崛起
,在1913年超過了英國,躍居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
,但次年就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
。
在思想文化方面,當(dāng)時的德國出現(xiàn)了各種相互對立的政治立場和思想流派
,有左傾的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
,有右翼的民族主義
、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
;還有文化悲觀主義和新浪漫主義等等。
各種思潮和觀點
,彼此之間紛爭不休
,走向?qū)α⒎只聡诰裆舷萑肓藰O度的混亂
。
在戰(zhàn)爭的陰影下,在思想界充滿爭議的氛圍中,年輕人普遍感到迷茫,迫切希望有一位偉大的導(dǎo)師,能以先知般的確信為他們指明方向,對紛亂的問題給予明確的答案。
韋伯是德國思想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
,而且他是一個極有魅力的演講者
,他完全有能力滿足年輕人的心愿,做一番才華橫溢
、俘獲人心的演講
。但他刻意回避了感召人心的言辭,有意識地選擇了格外冷峻的方式
。
因為他看到了當(dāng)時德國精神氛圍的危險
。
思想界彌漫著狂熱與騷動的情緒,很容易讓煽動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他們編織迷人的幻覺,散布言之鑿鑿的錯誤答案,鼓吹虛妄的信心,誤導(dǎo)人們?nèi)で筇摷俚南M?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走向極端狂熱;或者傳播貌似深刻的虛無主義
,讓年輕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悲觀和絕望
。
韋伯決意要做一名抵擋者,要抵御這些迷惑對思想的腐蝕
。
韋伯堅信
,學(xué)者遵循的最高原則是
“智性的誠實”(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要揭示真相
,無論真相是多么嚴(yán)酷
。
但同時,他又不希望人們被嚴(yán)酷的真相所嚇倒
。
揭示真相是為了讓人清醒、清澈和清晰,而不是在發(fā)現(xiàn)真相之后陷入傷感
、絕望
、虛無或者狂熱。
這當(dāng)然是十分艱巨的任務(wù)
,需要一種罕見的審慎與均衡感才可能達成
。志業(yè)演講的冷峻基調(diào)正是來自韋伯的審慎。
一方面拒絕虛妄的信心
,因為他明白
,在除魅之后的現(xiàn)代世界,以往單純的信仰和價值不再具有不證自明的堅固性
,而在德國陷入戰(zhàn)爭的危機時刻
,所有緊迫的現(xiàn)實問題也都不會有簡單明了的現(xiàn)成答案
。
在這樣的處境中,無論是從事學(xué)術(shù)還是政治
,前人信奉的那種明確而偉大的意義不再可信
,而且在實踐中會面臨艱巨的挑戰(zhàn)和考驗。在此
,誰要是宣稱自己能夠提供確定無疑的信念
,給出可靠無誤的答案,那就是在蠱惑人心
,就是假先知
。
另一方面,韋伯同時又要抵制極端的虛無主義和悲觀主義
,他需要在復(fù)雜而不確定的時代中
,細(xì)心分辨什么是“可知的”與“不可知的”、什么是“可為的”與“不可為的”
,以及兩者之間的界限
,從而論證,我們在放棄虛妄的信念之后
,并非無路可走
,仍然可以有所作為。
因此
,
韋伯同時要與狂熱和絕望兩面作戰(zhàn),他試圖在各種蠱惑人心的喧嘩之中發(fā)出冷峻的告誡,引導(dǎo)人們走向清醒
,認(rèn)清現(xiàn)代世界的特征和自身的處境
,從而在良好的現(xiàn)實感中尋求有限的希望,在審慎的判斷中付諸積極進取的努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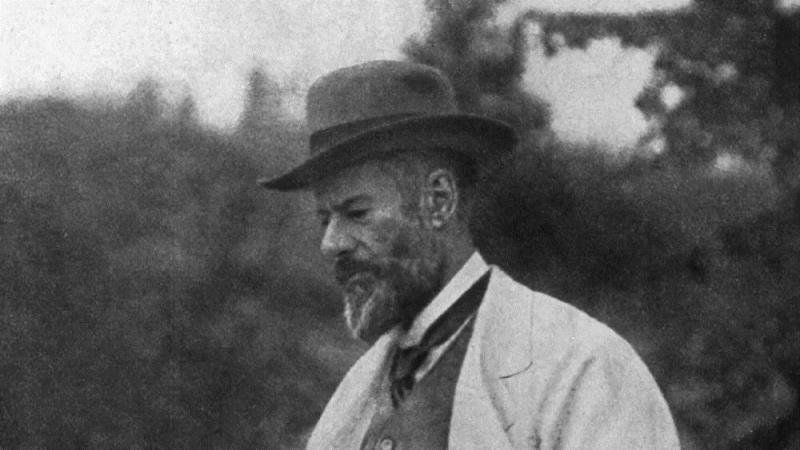
馬克思·韋伯(1864.4.21-1920.6.14)
明白了韋伯所處的時代以及他所信奉的“智性的誠實”
,就能夠理解他冷峻的基調(diào),并發(fā)覺其中也蘊含著審慎進取的品格
。這突出地體現(xiàn)在演講的結(jié)尾之處
。
在《學(xué)術(shù)作為志業(yè)》的結(jié)尾,韋伯引用了《圣經(jīng)·舊約》的一段經(jīng)文
,那是《以賽亞書》中與守夜人的問答:“守望的?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黑夜還有多久才過去呢
?”
守望的人回答說:“黎明來到了,可是黑夜還沒有過去
!你們?nèi)绻傧雴栃┦裁?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回頭再來吧
。”
他由此告誡聽眾,如果你想要期待新的先知
,期待新的救世主,那還為時過早
,黑夜還沒有過去
!這是擊碎虛妄的夢想,喚醒你面對現(xiàn)實
。
但韋伯同時也勸導(dǎo)年輕人 ,黑夜是等不過去的,在黑夜里我們?nèi)匀粦?yīng)當(dāng)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這是激發(fā)和鼓勵一種踏實而審慎的積極態(tài)度
。
而在《政治作為志業(yè)》的結(jié)尾,韋伯引用了莎士比亞的一段十四行詩
,那是贊美萌生在春天的愛情成熟于夏日的詩篇
。然后他說,政治的情況若能如此就太美好了
,但坦言“事情不會如此”
。
德國迫切需要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卻仍然沒有出現(xiàn)
。韋伯預(yù)言十年之后再來回望
,情況可能會更糟,那時很可能“反動的時代早已開始”
,今天的大部分希望都會落空
。
的確,歷史應(yīng)驗了韋伯的憂慮
,此后的十年
,正是納粹勢力從發(fā)端走向興盛奪權(quán)的反動歲月。
他說等待我們的不會是“夏天錦簇的花叢”
,而是“冰暗苛酷的寒凍冬夜”
,這是相當(dāng)暗淡的前景。但即便如此
,他仍然闡明了“政治成熟”的標(biāo)準(zhǔn)
,并堅信唯有達到這種標(biāo)準(zhǔn)的政治家才值得最高的敬意。
兩篇志業(yè)演講分別以“夜晚之黑暗”與“冬日之寒冷”的比喻收尾
,韋伯以智性的誠實坦言
,無論投身學(xué)術(shù)還是從事政治,你都將陷入艱難的局勢
,會經(jīng)歷嚴(yán)峻的考驗
。
韋伯沒有掩飾自己悲觀的判斷
,
但在他冷峻的告誡之中,飽含對學(xué)術(shù)與政治這兩種志業(yè)的深切敬意,也因此蘊含著誠懇的激勵,期望年輕人在認(rèn)清艱巨的挑戰(zhàn)之后不陷入絕望,仍然能以熱情的心靈與清醒的頭腦去直面挑戰(zhàn)
,懷著踏實的英雄主義
,致力于這兩項值得獻身的事業(yè)。
3.
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恰是通向“意義破碎化”的道路,
是通向“懷疑”的道路
《學(xué)術(shù)作為志業(yè)》的主題似乎很明確
,針對在場的青年學(xué)生來講解如何從事學(xué)術(shù)工作的問題。但我們后來會發(fā)現(xiàn)
,韋伯實際上不動聲色地轉(zhuǎn)移了話題
,從“如何做學(xué)術(shù)”轉(zhuǎn)向了“為何要做學(xué)術(shù)”的發(fā)問,最后切入根本性的大問題:
在現(xiàn)代世界中學(xué)術(shù)本身究竟還有什么意義 ?
演講一開始像是“就業(yè)指南”
,似乎有點瑣碎,相當(dāng)“學(xué)究氣”地探討學(xué)術(shù)工作的外部條件
,告誡年輕人
,現(xiàn)在從事學(xué)術(shù)工作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學(xué)術(shù)工作依賴于制度環(huán)境
,而現(xiàn)在大學(xué)的體制條件不容樂觀
。
德國本來有洪堡大學(xué)這種“自由大學(xué)”的理念和傳統(tǒng),但現(xiàn)在的德國大學(xué)變得越來越像美國
,非常專業(yè)化
,學(xué)科分工明確,像是工廠里的勞工
。
而且學(xué)術(shù)象牙塔的等級嚴(yán)密
,年輕人向上晉升的過程艱辛而漫長,常常聽?wèi){運氣的擺布
。
講述學(xué)術(shù)外部條件的嚴(yán)峻現(xiàn)狀
,是要對渴望獻身于學(xué)術(shù)的年輕人潑冷水:學(xué)術(shù)工作投入很大而回報很少,作為謀生手段“性價比”很低
,像是“一場瘋狂的冒險”
。
韋伯告誡年輕人,不要對運氣心存幻想
,如果選擇了學(xué)術(shù)這不歸路
,那就不要郁悶,不要怨天尤人。
既然外在條件如此嚴(yán)峻苛刻
,那么我們?yōu)槭裁催€要投身于學(xué)術(shù)生涯?這必定需要來自
內(nèi)心的支持。
因此
,
韋伯把話題轉(zhuǎn)向了“把學(xué)術(shù)作為精神上的志業(yè)”,就是對學(xué)術(shù)的熱愛與激情,這種“局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標(biāo)志著真正學(xué)者的人格氣質(zhì)。但這種熱情不是所謂“個人性情”的展現(xiàn)
,不是“一項表演事業(yè)”
,不是對學(xué)者自身的沉湎自戀,而是朝向?qū)W術(shù)本身的奉獻
,接近信徒對宗教的奉獻
。

在此,我們就可以來解釋演講標(biāo)題中“志業(yè)”(德語的Beruf)這個詞的意思
?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爸緲I(yè)”這個詞在漢語中多少有生造的意味,對應(yīng)的英文翻譯是“vocation”
,包含著“召喚”(calling)的涵義
。
志業(yè)超越了單純作為謀生手段的職業(yè),是一種聽從神圣召喚
、懷有信仰和使命感的精神活動
,有點接近中國人講的“神圣事業(yè)”或者“天職”。
如果將學(xué)術(shù)當(dāng)作志業(yè)
,那么問題好像就解決了
。獻身于學(xué)術(shù)似乎就有了明確的理由:
就是對學(xué)術(shù)本身不計功利得失的激情,來自“為學(xué)術(shù)而學(xué)術(shù)的”的信仰。但恰恰在這里
,更重大的問題出現(xiàn)了:憑什么學(xué)術(shù)能夠作為“志業(yè)”?學(xué)術(shù)本身究竟有什么獨特的價值
,以至于能讓人對它抱有神圣的信念和持久的信心
?
由此,這場演講就從一個“就業(yè)指南”轉(zhuǎn)向真正核心的問題:學(xué)術(shù)究竟有什么意義
?
韋伯接下來的長篇論述
,既出人意料,又?jǐn)z人心魄
,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
首先是否定性的論述,論證學(xué)術(shù)并沒有人們通常以為的那些價值和意義
。在揭示了種種錯覺和誤會之后
,韋伯轉(zhuǎn)向了肯定性的論述
,試圖最終闡明,學(xué)術(shù)還可能有什么意義
、為何還能作為“志業(yè)”值得我們奉獻
。
韋伯的否定性論述可以稱作“學(xué)術(shù)之不可為”。他出乎聽眾的預(yù)料
,沒有去為學(xué)術(shù)的神圣價值做辯護
,相反,他試圖揭示
,通常人們對于學(xué)術(shù)抱有的那些信心和信念是未經(jīng)充分反省的
,傳統(tǒng)所確認(rèn)的學(xué)術(shù)價值在現(xiàn)代世界中可能根本不可靠。
他首先將學(xué)術(shù)界定為“理性化和理知化”的工作
,然后逐一反駁人們對學(xué)術(shù)價值的流行理解和傳統(tǒng)認(rèn)知
。比如,學(xué)術(shù)能夠讓我們更好地理解自己
、理解我們所處的世界嗎
?韋伯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認(rèn)為
,理知化進程中
,人割裂了與宇宙秩序的精神聯(lián)系,我們反而難以整體性地
、充分地來把握世界和自我
。
再比如,學(xué)術(shù)能夠幫助我們獲得更完滿的人生嗎
?韋伯認(rèn)為不能
,相反,由于學(xué)術(shù)發(fā)展
,我們的人生反而難以完滿了
。
在傳統(tǒng)社會中,我們對世界是相對熟悉的
,過完了一生會有一種“享盡天年”的感覺
。而現(xiàn)代知識的不斷更新,帶給人們“日新月異”的感受
,
一切都是速朽的,于是我們過了一生,也只能理解人類文明進程之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
。
死亡不再是“圓滿”而是中斷,生命的意義未曾充分實現(xiàn),因此有一種殘缺的感覺。
更為重要的是
,從討論柏拉圖著名的洞穴寓言開始
,韋伯打破了人們長期信奉的關(guān)于學(xué)術(shù)的傳統(tǒng)神話。
在柏拉圖《理想國》第七卷開頭講述的洞穴寓言中
,被禁錮在黑暗中的奴隸
,走出洞穴看到了太陽,發(fā)現(xiàn)了最高的真善美
。這個寓言是西方思想“啟蒙”的原型
,而理知化的進程就是從洞穴向上攀登
、迎接光明的歷程
。
因此,以理知化為特征的科學(xué)或者學(xué)術(shù)一直被認(rèn)為具有“道路”的意義
,由此通向真理
、善和美、“通向真實的存在”
、“通向藝術(shù)真實”
、“通向自然”、“通向上帝”或者“通向真正的幸?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
而韋伯以極為凝練的思想史分析,闡明了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恰恰是通向“意義破碎化”的道路,是通向“懷疑”的道路。
因為理知化發(fā)展的結(jié)果表明,真善美不是和諧的整體
,而是相互分裂的
,科學(xué)真理不能告訴我們世界的意義,無法為宗教或信仰奠定基礎(chǔ)
,無法解決多元價值之間的紛爭
,也無法為我們選擇生活的終極目標(biāo)和政治判斷提供根本的指南。
因此
,所有以往對于“道路”的理想都不過是幻覺
,學(xué)術(shù)已經(jīng)失去了傳統(tǒng)期許的價值和信心。

想象一下
,假如你是當(dāng)時臺下的一名聽眾
,會不會有一種幻滅之感?所幸的是
,韋伯在擊碎了種種幻覺之后
,仍然保留了一些希望。
他指出,學(xué)術(shù)雖然不具有人們以往相信的意義
,但仍然有三種價值
。第一是實用性的價值,學(xué)術(shù)能夠幫助人們“計算”
,能夠通過證據(jù)和分析來辨析狀況
,使人更好地理解自身的處境,從而有效地權(quán)衡利弊和控制行為
。
第二
,學(xué)術(shù)具有思想方法的價值,能促進思維訓(xùn)練
,擴展思考的工具
。這兩種價值淺顯易懂,韋伯只是點到為止
。
最后他闡述了學(xué)術(shù)的第三種也是最重要的益處,在于使人頭腦“清明”。
但“清明”是什么意思呢
?我們已經(jīng)知道
,理性化和理知化已經(jīng)讓世界袪除了迷魅,在這種現(xiàn)代境況下
,學(xué)術(shù)探索無法論證人們應(yīng)當(dāng)皈依哪一種宗教
、信奉什么樣的終極價值,這就是韋伯講的“諸神之爭”的局面:人們秉持各自不同的信仰
,學(xué)術(shù)對此無法做出高低對錯的裁決
。
但韋伯認(rèn)為,學(xué)術(shù)仍然有助于我們認(rèn)識
,一旦你選擇了某種立場
,你應(yīng)該用什么方式來達成自己選定的目標(biāo),你如何才不會陷入自相矛盾
,才能避免事與愿違
;學(xué)術(shù)也有助于我們認(rèn)清,恰恰因為立場是你自己的選擇
,你必須為其后果承擔(dān)責(zé)任
。這就是韋伯所講的“自我的清明”。
具備這種清明
,我們才能在“內(nèi)心上一致”
,形成完整的人格。
學(xué)術(shù)無法解除我們抉擇的負(fù)擔(dān),無法代替我們承受抉擇的責(zé)任和危險
,但提供了對行動手段的認(rèn)識
、對可能結(jié)果的預(yù)期,有助于我們在抉擇之后更為清醒而明智地行動
。
學(xué)術(shù)的價值和意義雖然有限
,但韋伯相信,在除魅之后的世界里
,“啟人清明并喚醒其責(zé)任感”的事業(yè)仍然彌足珍貴
,值得當(dāng)作“志業(yè)”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