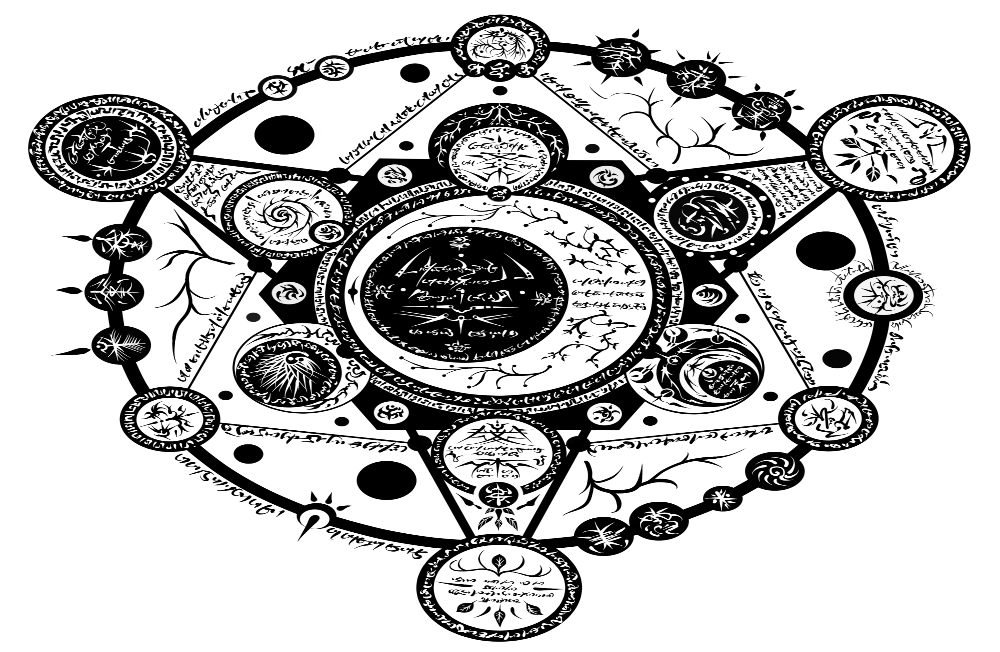一、巫術(shù)的定義
人們給巫術(shù)下過(guò)各種各樣的定義。盡管這些定義千差萬(wàn)別,
但它們都有一個(gè)基本的特征,即都 指出巫術(shù)是“基于一種對(duì)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并認(rèn)為人憑借這樣的力量可以控制周圍的世界” 。
然 而,
即使是西方人類學(xué)家也很難解釋巫術(shù)是什么。
以下是他們給巫術(shù)下的各種定義:
泰勒(E. B. Tylor)是這樣理解巫術(shù)的:
巫術(shù)是建立在聯(lián)想之上而以人類智慧為基礎(chǔ)的一種能力,但是在相當(dāng)大的程度上,
也是以人類 的愚鈍為基礎(chǔ)的一種能力。
這是理解魔法的關(guān)鍵。人類早在低級(jí)智力狀態(tài)中就學(xué)會(huì)了在思想中把那 些他己發(fā)現(xiàn)在實(shí)際中彼此相聯(lián)系的事物結(jié)合起來(lái)。
但是,
之后他就曲解了這種聯(lián)系,得出結(jié)論:聯(lián) 想當(dāng)然包括實(shí)際上的類似的聯(lián)想。
因而以此為指導(dǎo),
力圖用這種方法發(fā)現(xiàn)、預(yù)言和引出事變 ,
而這 種方法 ,
正如我們現(xiàn)在所看到的,只不過(guò)具有幻想的意義 。
根據(jù)蒙昧人 、
野蠻人和文明人廣泛眾多 的生活事實(shí),把想象的聯(lián)系誤認(rèn)為現(xiàn)實(shí)的聯(lián)系而產(chǎn)生的巫術(shù)可明顯地從其興起的低級(jí)文化到其高 。
另一個(gè)同樣有影響的巫術(shù)定義 ,
是由弗雷澤(Frazer)給出的,他將巫術(shù)定義為:
一種偽造出來(lái)的自然法則體系 ,
也是一套謬誤的行為準(zhǔn)則 ;
它是一種偽科學(xué),也是一種沒有成 效的技藝 。
巫術(shù)作為一種自然法則體系 ,
即關(guān)于決定世上各種事件發(fā)生順序的規(guī)律的一種陳述,可 稱之為 '理論巫術(shù)’ ;
而當(dāng)它作為人們?yōu)檫_(dá)到其目的所必須遵守的一套規(guī)則 ,
可稱之為“應(yīng)用巫術(shù)”。
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認(rèn)為 ,
以往的人類學(xué)家基本上把巫術(shù)定義為“感應(yīng)巫術(shù)” 。
他指 出,將巫術(shù)定義為“感應(yīng)巫術(shù)”犯了以偏概全的錯(cuò)誤 ,
因?yàn)橐粌煞N巫術(shù)不能涵蓋所有的巫術(shù)事實(shí)。
為此,莫斯對(duì)很多地區(qū)的巫術(shù)資料進(jìn)行考察。
通過(guò)泛文化研究,
他發(fā)現(xiàn)宗教和巫術(shù)截然不同:宗教儀式是公開的,
而巫術(shù)儀式卻要秘密進(jìn)行;巫術(shù)是沒有道德的,
而宗教則一定牽涉道德問(wèn)題;
巫術(shù)幾乎沒有教會(huì),而宗教則必須有教會(huì)。
莫斯根據(jù)這些特征將巫術(shù)定義為:“一切不屬于一種有組織的崇拜的儀式’是私下的、
秘密的、神奇的儀式,
它以違禁的儀式為界限。”這個(gè)定義的意義在 于,巫術(shù)不再被看作人類思維的一定狀態(tài)或一定階段,而是被看作一種社會(huì)現(xiàn)象。
馬林諾夫斯基(Malinnowski)為“區(qū)別巫術(shù)和宗教”,把巫術(shù)定義為“一套完全實(shí)用的行為,
為達(dá)到某種目的而采用的手段。”
埃文思·普里查德(E. Pritchard)認(rèn)為,只有當(dāng)巫術(shù)被看作是與經(jīng)驗(yàn)性活動(dòng)和信仰體系相關(guān)時(shí),
巫術(shù)才更容易理解。他說(shuō):“與其說(shuō)巫術(shù)主要是控制自然的工具,不如說(shuō)它是借助于為達(dá)到目的而 采取的經(jīng)驗(yàn)性措施的干預(yù),阻止與人的努力反其道而行之的妖術(shù)和其他神秘力量的工具。”
可見,想下一個(gè)適用范圍廣泛的定義,能足以包括人類學(xué)家希望在“巫術(shù)”的名義下加以描述 的人類行為的多樣性 ,
是十分困難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人類學(xué)家在巫術(shù)的界定上沒有達(dá)成某種共 識(shí) 。
哈維蘭(W.A. Haviland)說(shuō):“通過(guò)求助于某些明確規(guī)定的方式,能迫使超自然力量以某種方式為善的或者惡的目的起作用 。
這是經(jīng)典人類學(xué)的巫術(shù)概念 。
”
然而,也發(fā)現(xiàn)許多與超自然無(wú)關(guān)或者關(guān)系不大的巫術(shù)信仰 。
在許多地方流行這樣的說(shuō)法 ,
對(duì)某 人或某人好運(yùn)氣的夸獎(jiǎng)會(huì)破壞這個(gè)人的運(yùn)氣或給他帶來(lái)厄運(yùn)。如阿拉伯人認(rèn)為 ,
夸一個(gè)小孩漂亮有 可能給這個(gè)孩子帶來(lái)疾病或?yàn)?zāi)難 。
再如在印度、中東和歐洲某些地區(qū) ,
人們相信有些人的眼光是不 祥的 ,
必須躲避 ,
否則會(huì)遭受厄運(yùn)或疾病。這就是所謂的“邪惡眼” 。
二 、巫術(shù)研究譜系
在過(guò)去的一百多年里,西方人類學(xué)關(guān)于巫術(shù)的研究經(jīng)歷了一個(gè)明顯的變化過(guò)程。它的研究進(jìn)程 大致如下:
(一)巫術(shù)與宗教
一百多年前,弗雷澤發(fā)現(xiàn),凡與超自然力量有關(guān)的現(xiàn)象都可劃分為巫術(shù)和宗教兩大范疇。在他 看來(lái),宗教是對(duì)那些認(rèn)為能夠主導(dǎo)和控制自然與人生進(jìn)程的超人力量的勸解或撫慰,而巫術(shù)是操縱 某些己知自然法則的企圖。此后不久,很多人類學(xué)家認(rèn)為弗氏的分類法很有用,并開始強(qiáng)調(diào)使用這 一標(biāo)準(zhǔn),按他們自己的觀點(diǎn),把兩種不同范疇的現(xiàn)象區(qū)分開來(lái)。
涂爾干在(Emile Durkheim)《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書中指出,巫術(shù)與宗教截然不同。他 還提出了用來(lái)區(qū)分巫術(shù)和宗教的標(biāo)準(zhǔn)。宗教基本上是群體性的或集體性的事務(wù):沒有無(wú)教會(huì)的宗 教。巫術(shù)有顧客,但沒有教會(huì)。莫斯也把巫術(shù)和宗教截然分成兩個(gè)領(lǐng)域。在莫斯看來(lái),巫術(shù)具有 秘密性和個(gè)人性,巫術(shù)儀式通常在“偏僻的地方”舉行,而且經(jīng)常是由個(gè)人來(lái)完成。宗教則是社會(huì) 性,宗教儀式一般在教堂和信徒面前進(jìn)行。巫術(shù)不能使求助于它的人們團(tuán)結(jié)在一起,宗教能使信徒 結(jié)成一個(gè)具有同一的道德性團(tuán)體。
米沙。季捷夫(MischaTitiev)用“歲時(shí)禮儀”和“危機(jī)禮儀”來(lái)區(qū)分巫術(shù)和宗教活動(dòng)。他認(rèn)為,歲時(shí)儀式往往是周期性地舉行,在時(shí)間上提前通知,能使參與者有時(shí)間來(lái)培養(yǎng)一種共同的期待感而且歲時(shí)儀式總是社會(huì)性或社區(qū)性的,因而當(dāng)一個(gè)社會(huì)喪失了認(rèn)同感時(shí),原有的歲時(shí)儀式會(huì)走向消亡。與此不同的是,危機(jī)儀式習(xí)慣上是為滿足特定時(shí)刻的緊迫性需求而舉行,在時(shí)間上無(wú)法預(yù) 知,危機(jī)儀式不僅可以服務(wù)于全社會(huì)或較小的團(tuán)體也可以服務(wù)于個(gè)人,但它往往不是為了公共事務(wù),絕大多數(shù)的危機(jī)儀禮僅僅是由于私有財(cái)產(chǎn)或個(gè)人人身出現(xiàn)危機(jī)而舉行的,所以在許多方面危機(jī) 禮儀相當(dāng)接近于傳統(tǒng)的巫術(shù)概念,危機(jī)儀式在整個(gè)社會(huì)瓦解之后仍然能繼續(xù)存在許多時(shí)間,并且在新的社會(huì)條件下演變成大批的積淀物,這些積淀物就是宗教學(xué)者所說(shuō)的“迷信”。他的研究想要說(shuō) 明,許多附著于歲時(shí)儀式上的特質(zhì)是一些被看作宗教的東西,而許多與危機(jī)儀式相關(guān)的東西習(xí)慣上 則被看作是巫術(shù)。
然而,也有一些人類學(xué)家不接受弗氏對(duì)巫術(shù)和宗教所作的區(qū)分。他們發(fā)現(xiàn),宗教和巫術(shù)根本不 是彼此分離的,兩者之間有很多方面實(shí)際上是相重疊的,而且兩者間有著共同的基礎(chǔ)——對(duì)超自然 力量的信仰。因此,他們寧愿把這類活動(dòng)整體上稱為“巫術(shù)一宗教”活動(dòng)。馬雷特(RRMarett)認(rèn)為,在前萬(wàn)物有靈論階段,宗教與巫術(shù)相混合,后來(lái)巫術(shù)遭到組織化的宗教的譴責(zé)并獲得了一種指責(zé)性的含義后,宗教才與巫術(shù)區(qū)分開來(lái)。他說(shuō),在談?wù)撟诮虝r(shí),使用“巫術(shù)一宗教”這種說(shuō)法要 好一些。范根納普(VGennep)也不同意將巫術(shù)與宗教截然分開,而是將巫術(shù)看作實(shí)踐的方面, 宗教看作理論的方面,它們同屬于一個(gè)“巫術(shù)一宗教”混合體。

三、神秘的巫術(shù)
在宗教與巫術(shù)關(guān)系問(wèn)題上,弗思(Firth)顯得比較慎重。他說(shuō):“如果只使用一項(xiàng)標(biāo)準(zhǔn),巫術(shù)和宗教是容易區(qū)分的。但若是使用多種標(biāo)準(zhǔn)就不容易區(qū)分了。
最多只能在大體上說(shuō),
某一項(xiàng)行動(dòng)在 某種情況下發(fā)生,它主要的性質(zhì)是巫術(shù)的,
還是宗教的。
在極端的二者之間還有一種中間類型:巫 術(shù)和宗教的成分如此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以致可以把它的性質(zhì)稱為 '巫術(shù)一宗教’,
或是宗教一巫術(shù)。
事實(shí)上,這種中間類型是常見的。
”
(二)巫術(shù)的邏輯結(jié)構(gòu)
泰勒認(rèn)為巫術(shù)的邏輯基礎(chǔ)是一種錯(cuò)誤的聯(lián)想。
弗雷澤將這種錯(cuò)誤聯(lián)想歸結(jié)為:經(jīng)由類似產(chǎn)生聯(lián) 想,以此為據(jù)的順勢(shì)巫術(shù)或模仿巫術(shù);
以相互鄰近為依據(jù)的接觸巫術(shù)。
前者犯了把彼此相似之物視 為同一物的錯(cuò)誤,而后者犯了將相接觸過(guò)的東西看成為永遠(yuǎn)不再分離的錯(cuò)誤。
列維一布留爾(Levy — Bmhl)在《原始思維》一書中,
把社會(huì)劃分為兩種主要類型,即原始 社會(huì)和文明社會(huì),
與之相適應(yīng)有兩種相互對(duì)立的思維方式:原始思維和文明思維。
他確認(rèn)原始思維 是“原邏輯的”,受神秘“互滲律”支配,以超自然為取向。列維一斯特勞斯(Claude Levi — Strauss)不同意布留爾的上述觀點(diǎn),他認(rèn)為,原始思維與現(xiàn)代思維在思維結(jié)構(gòu)上是相同的,沒有本 質(zhì)上的區(qū)別。列維一斯特勞斯認(rèn)為,科學(xué)思維有兩種模式:“其中一個(gè)大致對(duì)應(yīng)著知覺和想象的平 面,另一個(gè)則是離開知覺和想象的平面。似乎通過(guò)兩條不同的途徑都可以得到作為一切科學(xué)的——不論是新石器時(shí)代的或是近代的——對(duì)象的那些必要聯(lián)系:這兩條途徑中的一條緊鄰著感性直觀,另一條則遠(yuǎn)離著感受性直觀。”列維一斯特勞斯要說(shuō)明的是巫術(shù)與科學(xué)是本質(zhì)相同的思維過(guò)程,代表著科學(xué)思維的兩種模式。“我們最好不要把巫術(shù)和科學(xué)對(duì)立起來(lái),
而應(yīng)把它們比作獲取知識(shí)的兩種平行的方式……與其說(shuō)二者在性質(zhì)上不同,不如說(shuō)它們只是適用于不同種類的現(xiàn)象。
”
埃文思?普里查德的《阿贊德人的巫技、
神諭和巫術(shù)》(1937)說(shuō)明妖術(shù)如何為因果鏈中“缺失的環(huán)節(jié)’提供了解釋。那些由于粗心大意或違反禁忌造成的事件并不被說(shuō)成妖術(shù)之過(guò)。只有那些不 常見、
不能按常規(guī)因果關(guān)系來(lái)理解的事件,
才歸咎于妖術(shù)。在他看來(lái),
阿贊德人的妖術(shù)觀念是一種獨(dú)立的“封閉的”思想體系,
它對(duì)災(zāi)禍所作的解釋,是不能按照西方的歸納證明概念加以驗(yàn)證的。
坦比亞(SJ°Tambiah)對(duì)阿贊德人巫術(shù)行為中潛隱著的邏輯思維作了富有洞察力的探討。
他認(rèn)為,巫術(shù)思維和科學(xué)思維都是以類比為基礎(chǔ),
但科學(xué)運(yùn)用類比依靠的是事物與其性質(zhì)之間的因果關(guān) 系,
它是根據(jù)己知的因果關(guān)系去推知相似但未知的因果關(guān)系;巫術(shù)的類比依靠的卻是將一套關(guān)系中 內(nèi)含的價(jià)值或意義勸導(dǎo)性地轉(zhuǎn)換到另一套關(guān)系中去,
而不管這兩套關(guān)系間有沒有相似之處或因果聯(lián) 系。
由于運(yùn)用的是兩種不同的類推,故巫術(shù)和科學(xué)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思維類型,
對(duì)兩者不能也不應(yīng) 用同一標(biāo)準(zhǔn)去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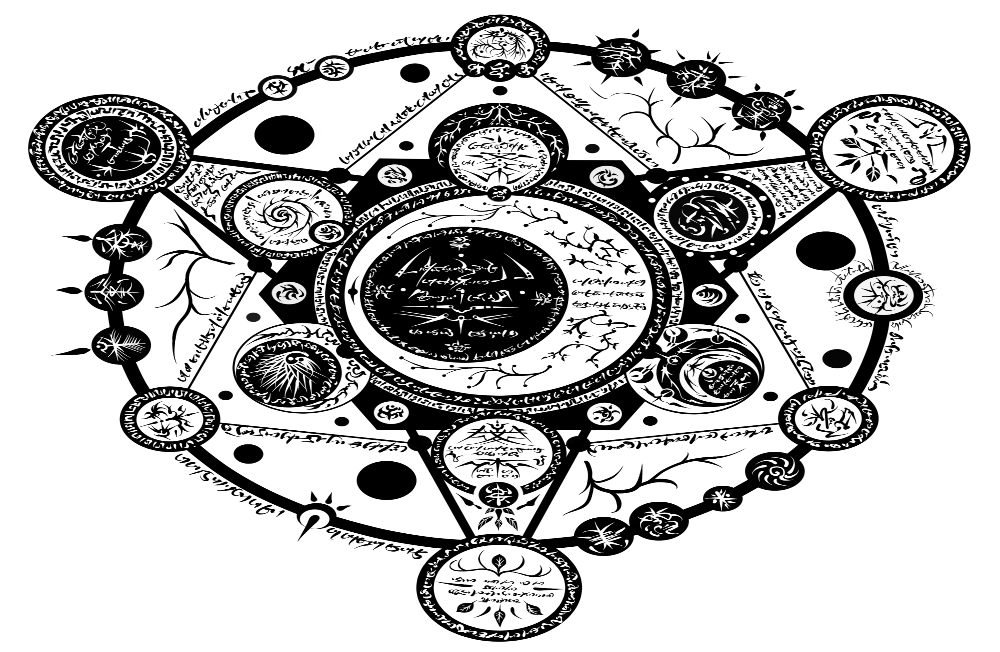
(三)巫術(shù)的功能與社會(huì)結(jié)構(gòu)
早期的人類學(xué)巫術(shù)研究,可歸到比較文化視野下的“異文化”研究范疇。
其研究主要是對(duì)“未 開化野蠻人”巫術(shù)、
方技的搜集。后來(lái)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的“功能學(xué)派”的人類學(xué)巫術(shù)研究逐漸失去了對(duì)這一范式的熱情,
而著重于巫術(shù)的功能。
馬林諾夫斯基將巫術(shù)與人類和自然相互關(guān)系這一“功能”直接相連。他宣稱所有的巫術(shù)都是為 了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
巫術(shù)總執(zhí)行著這樣一種原則:“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
”人們?yōu)榱嗣鎸?duì) 那些無(wú)法預(yù)知的不幸情形和境地,不可避免地會(huì)與巫術(shù)發(fā)生關(guān)系。
巫術(shù)需要儀式行為的表演來(lái)幫助 人們實(shí)現(xiàn)生活中所辦不到的、
無(wú)法取得的結(jié)果。馬林諾夫斯基非常清晰地演繹出巫術(shù)的“功能主 義”意義:巫術(shù)可以幫助人們實(shí)現(xiàn)自身所不能達(dá)到的目的 。
拉德克利夫 。
布朗(Radcliffe
Brown)則從巫術(shù)儀式及巫術(shù)儀式價(jià)值與社會(huì)基本結(jié)構(gòu)出發(fā),探 討巫術(shù)的基本功能 。
他認(rèn)為 ,
巫術(shù)儀式的功能在于它通過(guò)反復(fù)地向人們灌輸那些對(duì)于完成重大任務(wù) 和承擔(dān)不可推卸的重任,使之內(nèi)在化價(jià)值 、
思想感情和態(tài)度等 ,
從而維系了社會(huì)的結(jié)構(gòu)。
因此,巫 術(shù)的功能不但包含了巫術(shù)對(duì)于個(gè)體的需要,
而且上升為維護(hù)集體利益的需要,是社會(huì)制度的需要。
人類學(xué)家在非洲社會(huì)研究中有效地使用過(guò)一種“張力測(cè)量”理論。
根據(jù)這項(xiàng)理論,巫術(shù)指控的爆發(fā)、
女巫尋找活動(dòng)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對(duì)劇烈社會(huì)矛盾的一個(gè)反映。
如埃文斯·普里查德的《阿贊 德人的巫技、神諭和巫術(shù)》一書向我們展示,
在阿贊德人的生活中,
妖術(shù)處處起著作用。狩獵、
捕 魚、
農(nóng)耕、家庭生活、
地區(qū)性或院落性的集體生活,
到處都可見到妖術(shù)的影響。任何人任何時(shí)候在任何生活過(guò)程中遇到了任何失敗或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