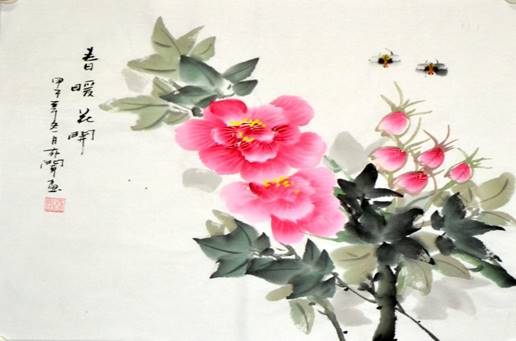一 、
道以氣顯、道由心成的道氣心一體論對(duì)道教的影響
《莊子》不僅將“道”作為最重要的概念 ,而且還通過(guò)基于“道”的宇宙論和修養(yǎng)論明確將“道”與“氣”
、“心”關(guān)聯(lián)起來(lái)?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肚f子》書(shū)中很多地方論“道”兼論“氣”
、“心”,這使
《莊子》中的“道”、“氣”、“心”之間總處于一體關(guān)聯(lián)的整體之中,道以氣顯,道由心成?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肚f子》的這種道氣心一體論對(duì)后世道教道論的演變起了重要的先導(dǎo)作用。
關(guān)于“道以氣顯”,《知北游》說(shuō):“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故曰:‘通天下一氣耳’。” “通天下一氣”旨在強(qiáng)調(diào)萬(wàn)物生滅的整體過(guò)程只是“氣”的本然流變,“道”的“自然”本性也由此而得以透顯。因此《莊子》“通天下一氣”的氣論思想總和道論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它不過(guò)是闡釋“道”之自然本性的一種方式。同樣的情形我們還可以在《至樂(lè)》中看到,莊子在解釋為何其妻死自己卻鼓盆而歌時(shí)說(shuō):“察其始而本無(wú)生,非徒無(wú)生也而本無(wú)形,非徒無(wú)形也而本無(wú)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 ,氣變而有形
,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
,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shí)行也。
”《至樂(lè)》篇認(rèn)為人的生死不過(guò)是“氣”之狀態(tài)的改變,這就像春夏秋冬的交替一樣自然,在此意義上《至樂(lè)》把對(duì)這種生死自然的認(rèn)識(shí)稱(chēng)為“通乎命”?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梢?jiàn),上述《莊子》書(shū)中的氣論思想不過(guò)是凸顯萬(wàn)物流變過(guò)程中所含具和昭示的本然之“道”的手段
,通過(guò)以氣顯道,“道”的自然本性就被表露無(wú)疑
。

關(guān)于“道由心成”,《應(yīng)帝王》說(shuō):“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yīng)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汝游心于淡,合氣于漠?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span>
“用心若鏡”、“游心于淡”作為體道者的境界或修養(yǎng)方法,它強(qiáng)調(diào)的是去掉“心”的人為妄作而合于無(wú)為空明的虛靜之道,也即以“心”合“道”。這表明“心”總是存在和“道”相貫通的可能性通道,在“心”的現(xiàn)實(shí)狀態(tài)中總潛含著合于“道”之本性的方面。只有如此,以“心”合“道”才成為可能。正是由于“心”存在著和“道”相貫通的可能,所以莊子才反對(duì)“勞形怵心”,莊子后學(xué)也告誡人們“無(wú)攖人心”。這其實(shí)都是要求保有“心”所本具的與“道”相合的自然本性
,反對(duì)一切對(duì)“心”之自然狀態(tài)的人為扭曲
。同時(shí)《莊子》的“心”還有另外的意義
,如莊子在《齊物論》中所描繪的“日以心斗”、“有蓬之心”等
,這種意義上的“心”是指與“道”之本性相背離的狀態(tài)
,它的特點(diǎn)是游離了“道”的無(wú)為和虛淡,這又使以“心”合“道”成為必要
。
至此我們可以說(shuō),《莊子》中所說(shuō)的“心”大體上含具兩種可能的趨向:一與道相合,一與道相違
。盡管《莊子》關(guān)于這方面的論述還顯得籠統(tǒng)
,“心”的這兩種含義在《莊子》中還是“混成”的
,并不像后來(lái)道教對(duì)“心”的區(qū)分那樣明顯
(照心、動(dòng)心、真心、妄心、道心、人心),但這并不妨礙從修養(yǎng)論的角度使“修心”既可能又必要。事實(shí)上《田子方》中就提出了“修心”的概念:“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span>
文中“修心”的“心”同時(shí)具有上述“心”的兩種含義,所謂“修心”即指摒棄偏駁的人為之心、世俗之心而達(dá)致“心”的“以明”狀態(tài)。
如果說(shuō)“道以氣顯”、“道由心成”分別從兩個(gè)方面揭示了“道”與“氣”、“道”與“心”的聯(lián)系,那么《人間世》的“心齋”之法則直接表露了“道”、“氣”、“心”之間的
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人間世》說(shuō):“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唯道集虛,虛者
,心齋也
”,以“虛而待物”來(lái)概括“氣”的特征,可見(jiàn),“虛”
(空明)乃是“氣”的本性;“虛者心齋”表明“心齋”是達(dá)致“虛”之狀態(tài)的手段
,“虛”乃是“心齋”的結(jié)果和境界
;
“唯道集虛”中的“集”有生發(fā)的意思,“唯道集虛”說(shuō)明“虛”的生發(fā)和呈顯依賴(lài)于“道”。這樣
,在《莊子》的“心齋”之法中,“氣”
、“心”和“道”就以“虛”為中介發(fā)生了深刻的
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作為“氣”之特性的“虛”可以由“心齋”來(lái)達(dá)致
,可以由“道”來(lái)呈顯
,因而“道”、“氣”
、“心”三者就處于整體關(guān)聯(lián)之中,具有某種
內(nèi)在同一性。
由此可見(jiàn),
《莊子》書(shū)中的“道”、“氣”
、“心”處于一體關(guān)聯(lián)之中,道以氣顯
,道由心成。
盡管《莊子》對(duì)“道”、“氣”
、“心”的關(guān)系缺乏詳細(xì)論述
,但這種道——?dú)狻牡囊惑w結(jié)構(gòu)和潛含于其中的“道”、“氣”
、“心”之間的
內(nèi)在同一性構(gòu)成了道教道論演變的邏輯前提。
道教道論經(jīng)歷了以氣釋道的道氣論、以心釋道的道心論
、整合道氣論與道心論的
內(nèi)丹性命學(xué)三個(gè)階段,如果從道家哲學(xué)中去追尋道教道論的邏輯演變的話(huà),《莊子》揭示的道氣心一體論無(wú)疑是最初的源頭。莊子“道以氣顯”的思想構(gòu)成道教道論的第一個(gè)形態(tài)——道氣論的源頭
。道氣論對(duì)莊子“道以氣顯”的發(fā)展是通過(guò)兩種思路來(lái)進(jìn)行的:一是以氣為道
,一是在道生論中援氣實(shí)道
。這兩種情形分別可以在《
老子想爾注》和《老子
道德經(jīng)河上公章句》中看到
。《老子想爾注》已將“道”
、“氣
(炁 )”連稱(chēng):“道氣在間,清微不見(jiàn)”;“道炁常上下,經(jīng)營(yíng)天地
內(nèi)外?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薄独献酉霠栕ⅰ愤€將“道”稱(chēng)為“一”,“一者
,道也”,又認(rèn)為“一散形為氣
,聚形為太上老君”
,可見(jiàn)在《老子想爾注》中
,“道”和“氣”
(炁)可以等同 ,這是以氣為道的路子。

《老子道德經(jīng)河上公章句》則說(shuō):“一者 ,道所始生,太和之精氣也”,這是把“精氣”看作“道”的派生物
,用氣論對(duì)“道”的
內(nèi)容加以充實(shí),可以稱(chēng)之為援氣實(shí)道 。
道氣論的確立使得各種煉氣之術(shù)在道門(mén)中盛行 ,《太平經(jīng)》就對(duì)于以氣論為依據(jù)的“守氣”、“食氣”等修養(yǎng)方法有細(xì)致的說(shuō)明
。葛洪在《抱樸子
內(nèi)篇》中對(duì)行氣法曾給予很高評(píng)價(jià),認(rèn)為行氣乃是得道的重要手段:“欲求神仙 ,唯當(dāng)?shù)闷渲烈?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至要者在于寶精行氣
,服一大藥便足
。”《云笈七簽》卷五十六至六十二就有關(guān)于隋唐前后“諸家氣法”的總結(jié)
,這表明了作為隋唐之際道教煉養(yǎng)理論主要支撐的道氣論在當(dāng)時(shí)的顯赫地位
,建立在道氣論基礎(chǔ)之上的服氣
、養(yǎng)氣、導(dǎo)引
、行氣、食氣
、煉氣等各種氣法也曾一度在道教中達(dá)到鼎盛
。
道氣論的盛行在推動(dòng)道教煉養(yǎng)術(shù)發(fā)展的同時(shí),也有著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
,因?yàn)闊o(wú)論是將“氣”等同于“道”還是用“氣”來(lái)充實(shí)“道”,都有一個(gè)共同的理論缺陷
,即削弱了“道”的終極超越性。因此道氣論只能強(qiáng)化而無(wú)法突破道教肉體長(zhǎng)生的理念
。而令
道家中人自豪的是,肉體長(zhǎng)生的目標(biāo)已在道教煉養(yǎng)中被證實(shí)(丹道修煉通過(guò)將肉體轉(zhuǎn)化為“炁”而達(dá)到肉體以先天一炁的形式長(zhǎng)生久視)。
在佛教心性論的刺激下,《莊子》等原始道家中隱含的道心論萌芽在隋唐之際逐漸被復(fù)活和強(qiáng)化,這一時(shí)期道教道論由道氣論向道心論轉(zhuǎn)化,在這一轉(zhuǎn)化過(guò)程中,早期重玄學(xué)家的道性論起了過(guò)渡作用。以重玄學(xué)“道性”說(shuō)和修心理論為依托,隋唐的重玄學(xué)者對(duì)“道”的解釋逐漸轉(zhuǎn)向“心” 、“性”的角度
。司馬承禎指出:“心源是元始
,更無(wú)無(wú)上道”
,又說(shuō):“源其心體,以道為本
。”
司馬承禎把“道”等同于“心源” ,并認(rèn)為“道”乃是心之本體
,這里的“心源”、“心體”都已帶有明顯的心本論意昧
,標(biāo)志著道心論在道教理論中的確立。之后杜光庭則進(jìn)一步將道心論貫徹到修養(yǎng)論中去
,明確指出“修道即修心也”
,“修心即修道也”。以心釋道的道心論確立后
,進(jìn)一步和早期重玄學(xué)道性論相融合,最終產(chǎn)生了道教心性學(xué)
。

當(dāng)?shù)澜虒W(xué)者將道氣論和道心論在道教傳統(tǒng)的形神觀(guān)視野下加以整合,就誕生了不同于以往道氣論和道心論的嶄新理論形態(tài)—— 內(nèi)丹性命學(xué)。在內(nèi)丹學(xué)中,“心”與“神”、“性”、“氣”與“命”往往并稱(chēng)并在同一意義上被使用,即所謂“氣是形中命,心為性內(nèi)神?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本哂行紊弦饬x的“氣”
(先天命)和“心”(先天性)被整合在內(nèi)丹學(xué)的道論之中,“性”和“命”成為同一道體在兩種維度上的呈顯,道體涵攝著“性”(心)、“命”(氣)這兩端。內(nèi)丹學(xué)的這種觀(guān)點(diǎn)同《莊子》所表露的道氣心一體論有著精神實(shí)質(zhì)上的一致。
內(nèi)丹學(xué)家這樣表述道體和“心”(性)、“氣”(命)的關(guān)系:“無(wú)為則能見(jiàn)無(wú)名之妙,全其性也,有為則能見(jiàn)有名之徼,全其命也,有與無(wú),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有無(wú)交入,性命雙全也。”在這里,“心”(性)和“氣”(命)作為“有無(wú)”具有“同出而異名”的特點(diǎn),并且在煉養(yǎng)論上“有無(wú)交入”、“性命雙全”的目標(biāo)就是要實(shí)現(xiàn)“性”、“命”和“道”的混融,
這表明自《莊子》所肇始的道氣心一體的結(jié)構(gòu)到內(nèi)丹學(xué)這里得到了升華和徹底的完成。
在道教道論的演變中,無(wú)論是道氣論還是道心論,亦或在這兩者基礎(chǔ)之上整合而成的內(nèi)丹性命學(xué),我們都可以從《莊子》的道氣心一體論中找到源頭。就理論實(shí)質(zhì)而言,如果從道家道教內(nèi)部自身的理論發(fā)展來(lái)看,從道教道氣論到道心論乃至內(nèi)丹性命學(xué)的演變不過(guò)是對(duì)《莊子》中“道”、“氣”、“心”關(guān)系的深化和發(fā)展。
二、“體道”、“守宗”、“得道”的體道論對(duì)道教的影響
先秦道家中《莊子》最早提出“體道”、“得道”、“守宗”的概念。《知北游》說(shuō):“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治道”都是將超越的“道”作為人之存在狀態(tài)的理想趨歸
。關(guān)于“得道”,《大宗師》說(shuō):“夫道
,有情有信,無(wú)為無(wú)形
;可傳而不可受
,可得而不可見(jiàn);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神鬼神帝
,生天生地
;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
,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
,先天地生而不為久
,長(zhǎng)于上古而不為老?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钡乐坝星橛行拧北砻鳌暗馈钡膶?shí)存性,因此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的人來(lái)說(shuō)
,超越之“道”并非虛無(wú)縹緲
,事實(shí)上這段話(huà)就明確表明了“道”的“可得”性。不僅如此
,《在宥》篇還借
廣成子之口強(qiáng)調(diào)“得道”的重要性:“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
;失吾道者
,上見(jiàn)光而下為土
?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span>
值得注意的是,在莊子及其后學(xué)看來(lái),這種可得之“道”并不是外在于人的某種對(duì)象性存在,所以《天運(yùn)》篇提醒人們說(shuō):“使道而可獻(xiàn),則人莫不獻(xiàn)其君
;使道而可進(jìn),則人莫不進(jìn)之于其親
;使道而可以告人
,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
,則人莫不與其子孫?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span>
可見(jiàn),“道”根本就不是一種與人的存在無(wú)關(guān)的對(duì)象物
。
《莊子》的“得道”實(shí)際上就是要求摒棄一切人為的矯飾,與道的自然狀態(tài)相契合。
關(guān)于“守宗”,《大宗師》說(shuō):“審乎無(wú)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边@里的“宗”是指與相對(duì)而變易的經(jīng)驗(yàn)事物相對(duì)立的“道”,因此“守宗”其實(shí)就是“守道”
?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傊?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莊子》書(shū)中的“體道”
、“得道”、“守宗”都是一些道學(xué)修養(yǎng)命題
,是指以“道”來(lái)充實(shí)和確立人的生存狀態(tài)。

《莊子》的“體道” 、“得道”
、“守宗”思想對(duì)后世道教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這首先表現(xiàn)在它塑造了道教以術(shù)證道
、術(shù)道合一的特點(diǎn)。道教將《莊子》“體道”
、“得道”的哲學(xué)命題加以實(shí)證化
,將之作為修道的原則和目標(biāo),并以此為基礎(chǔ)開(kāi)出了豐富的修煉方法
。“體道”就是“體證”道
,可以說(shuō)
,道門(mén)中的一切方術(shù)都是對(duì)終極之道進(jìn)行體證的一種手段。
《莊子》“守宗”的哲學(xué)命題也被道教變成具體的方法,《老子想爾注》就強(qiáng)調(diào)“守道誡”的重要性:“今布道誡教人,守誡不違
,即為守一矣”
;“仙士畏死,信道守誡
,故與生合也?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span>
這里的“守誡”、“奉誡”不過(guò)是《莊子》“守宗”
(道)的另外版本。不僅如此,“守宗
(道)”也被看成道教養(yǎng)生的根本原則:“養(yǎng)生者慎勿失道,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與生相守
,生與道相保
,二者不可相離
,然后乃長(zhǎng)久
。”這種
“生道合一”的思想仍然是莊子“守宗(道)”命題的落實(shí)轉(zhuǎn)化 。
《莊子》“得道”的命題則被直接轉(zhuǎn)化成道教的證真目標(biāo),“得道” 、“合道”成為道教一切煉養(yǎng)術(shù)的終極標(biāo)的
。這樣,道教以“得道”為究竟
,以“體道”為手段,使自身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實(shí)證意味
,以術(shù)證道也由此而成為道教的鮮明特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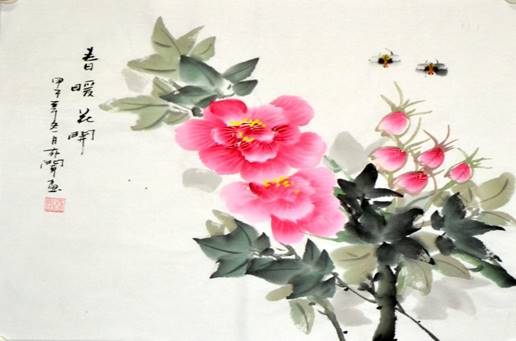
《莊子》“體道”、“得道” 、“守宗”的思想被道教所繼承,成為道教煉養(yǎng)不可撼搖的原則
,這一原則對(duì)道教煉養(yǎng)術(shù)起了重要的范導(dǎo)作用
。道教產(chǎn)生后,雜多的“術(shù)”和超越的“道”之間的貫通就成為必需
,唯有如此,“以術(shù)證道”才是可能的
。這一方面需要道教對(duì)各種道術(shù)進(jìn)行理論論證
,另一方面也要求道教對(duì)駁雜的道術(shù)進(jìn)行錘煉、篩選和實(shí)證
,這兩者都必須緊緊圍繞“體道”
、“得道”
、“守宗”這一道教煉養(yǎng)的總原則和目標(biāo)來(lái)進(jìn)行
。
以“得道”的終極目標(biāo)為依據(jù),道教在發(fā)展中逐漸對(duì)各種道術(shù)有了清晰的界定,曾經(jīng)在道門(mén)中盛極一時(shí)的“寶精”、“行氣”
、“導(dǎo)引”
、“辟谷”、“服食”
、“黃白”等道術(shù)在道教理論的成熟階段——
內(nèi)丹學(xué)誕生之后均受到了批判。張伯端就曾站在內(nèi)丹學(xué)立場(chǎng)上對(duì)“服氣”、“存想”、“導(dǎo)引”、“持咒”、“符篆”、“辟谷”、“房中”、“服食”、“外丹”等道教傳統(tǒng)煉養(yǎng)術(shù)進(jìn)行過(guò)批判,張伯端認(rèn)為“以上諸法,于修身之道,率多滅裂,故施力雖多而求效莫驗(yàn)。若勤心苦志,日夕修持 ,止可以辟病
,免其非橫
。一旦不行,則前功漸棄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睆埐酥詫?duì)道教傳統(tǒng)煉養(yǎng)術(shù)進(jìn)行批判
,就是因?yàn)檫@些傳統(tǒng)的道教體證方法無(wú)論理論上還是實(shí)踐上均與道教“得道”的目標(biāo)相左
,即無(wú)法實(shí)現(xiàn)“術(shù)”和“道”的真正貫通。
宋代李道純對(duì)道教煉養(yǎng)術(shù)進(jìn)行了系統(tǒng)總結(jié) ,將
內(nèi)丹學(xué)之前的煉養(yǎng)術(shù)分為“傍門(mén)九品”。其內(nèi)容涉及“房中采補(bǔ)”、“外丹服食”、“辟谷”、“服餌”、“持齋”、“吞霞”、“服氣”、“存思注想”、“三歸五戒”等。李道純認(rèn)為這些修行方法均屬“傍門(mén)”,無(wú)法得道。道教人士之所以自覺(jué)對(duì)道教煉養(yǎng)術(shù)進(jìn)行反省和修正,根本上來(lái)源于從《莊子》秉承而來(lái)的“體道”、“得道”、“守宗”思想的影響?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體道”、“得道”、“守宗”作為道教煉養(yǎng)的根本原則還確保和推動(dòng)了道教宗教精神的最終確立。道教的神仙追求所固有的浪漫情結(jié)以及道教“得道”的證真目標(biāo)都已預(yù)定了道教宗教精神的超越特質(zhì)。但道教誕生后的相當(dāng)長(zhǎng)的一段時(shí)間內(nèi),底層普羅大眾及外界某些二流學(xué)者以為“得道”的目標(biāo)和神仙理想就是長(zhǎng)壽不死(如佛教對(duì)道教給以“守尸鬼”的誤解,正是自身缺乏深入實(shí)修,長(zhǎng)期以來(lái)對(duì)生命的認(rèn)識(shí)嚴(yán)重偏頗而造成的偏見(jiàn);除道家以外,一切宗教的致命缺點(diǎn)和要害,都在于過(guò)分重視心靈的形而上修養(yǎng),而缺乏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命的直面與認(rèn)識(shí)
),這是不對(duì)的
,因?yàn)檎嬲牟凰朗侵溉怏w經(jīng)過(guò)轉(zhuǎn)化,升華為先天一炁(
這就是當(dāng)代物理學(xué)里面的“物質(zhì)轉(zhuǎn)化為能量”公理),炁是無(wú)形而永恒存在的,所以稱(chēng)之為“長(zhǎng)生”。民間業(yè)余的認(rèn)識(shí)
,實(shí)際拒斥并消解了道教精神超越的普世性
,殊為可惜
。
道教在自身發(fā)展中,正是借助于源于《莊子》的“體道”、“得道”、“守宗”這一道教煉養(yǎng)的總原則才得以逐步成熟肉體長(zhǎng)生的理念及實(shí)證。
道教理論家以隋唐重玄學(xué)心性論為基點(diǎn),將超越之“道”和道教的“神氣”、“性命”概念整合在一起,逐步開(kāi)出內(nèi)丹性命學(xué),使人的經(jīng)驗(yàn)存在狀態(tài)和超越的得道境界之間有了切實(shí)的橋梁,即所謂“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煉虛合道”的煉養(yǎng)程序,從而使內(nèi)丹學(xué)在終極境界上表現(xiàn)出向莊老復(fù)歸的傾向。這種復(fù)歸并不僅僅是借鑒了莊老中的個(gè)別修養(yǎng)方法,而是就“得道”的終極旨趣而言真正和莊老有了理論上的銜接,因而這種復(fù)歸才具有實(shí)質(zhì)的意義。當(dāng)傳統(tǒng)道教肉體不死的理念被內(nèi)丹學(xué)“了性了命”的嶄新表達(dá)語(yǔ)言,道教超越的宗教精神才得以真正普世——雖然這二者本質(zhì)仍然的一致的。
這些過(guò)程在根本上來(lái)源于從《莊子》那兒所承續(xù)的“體道”、“得道”、“守宗”這一原則的推動(dòng)。

三、“反性”
、“復(fù)初”的復(fù)道論對(duì)道教的影響
在《莊子》哲學(xué)中,“道”作為人的本真生存狀態(tài),往往因世俗生活的陷溺而受到遮蔽,所以必須使人超拔于世俗生活之上而返歸于“道”這種人之原初而理想的生存狀態(tài),這就是《莊子》中提到的“反性”和“復(fù)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