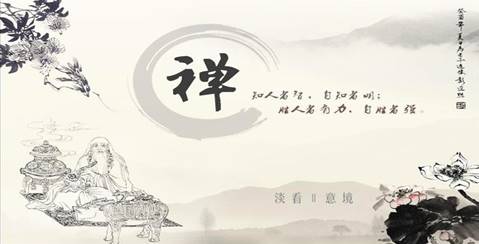復歸于無極
——志同道合的武術(shù)與道家
喬鳳杰
|
道的彰顯,也就是人們對道術(shù)的真正掌握,是在對現(xiàn)有技術(shù)的反復實踐中超越實現(xiàn)的。道,是自己理想技術(shù)產(chǎn)生的根源;前人留傳下來的技術(shù),則是后人悟道的基礎與媒介 。
|
道家對道這一超驗心的崇尚 ,為傳統(tǒng)武術(shù)訓練確立了一個極具誘惑的終極目標
,并使習武者對自身潛在的超常能量充滿信心
。道家之“復歸于無極”的基本思路
,完全可以被作為傳統(tǒng)武術(shù)之超級心理訓練的根本原則;作為其“復歸于無極”的彰顯超驗心的專業(yè)方式,道家煉養(yǎng)的技術(shù)與理念
,分別被某些拳種吸收改造成了內(nèi)功功法與技戰(zhàn)術(shù)訓練的指導理論。
1、復歸的理路
作為一種超驗心,在老子的思想系統(tǒng)中,道即是自然道即是無待,而且道既是無也是有。既是無,也是有,可能是道這個概念最耐人尋味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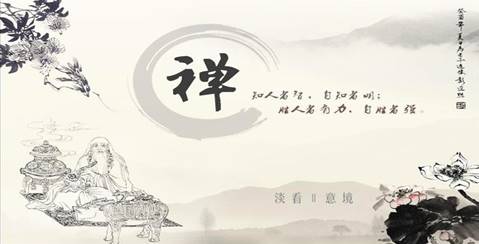
無即沒有任何的造作私為與偏執(zhí)成見。它既可以表示去除造作私為與偏執(zhí)成見的過程,也可以表示去除造作私為與偏執(zhí)成見之后的主體境界。道,乃是去除一切造作私為與偏執(zhí)成見以后,在沒有任何的造作私為與偏執(zhí)成見境界中顯現(xiàn)出來的超驗心。既然“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無化”之后顯現(xiàn)出來的道乃是天地萬物得以正常生長、發(fā)育、衰落、死亡的根據(jù),那么,這種“無化”之后顯現(xiàn)出來的道,自然即是最完美的有。從這個角度講道既是無也是有,乃是無與有的統(tǒng)一體。說道是有,強調(diào)道是最完美的有,只是為了表明道對于人類的現(xiàn)實意義
。
既然道是“無化”掉一切經(jīng)驗與“他然”以后的一種主體境,那么,道
、無、自然
、一
,等等,其實都是一回事
。對經(jīng)驗世界的“無化”
,必然意味著對超驗世界的彰顯;去除經(jīng)驗心以及由經(jīng)驗心而建構(gòu)的現(xiàn)象世界以后
,彰顯出來的必然是真實的超驗心以及物自身的世界
。正是這種被彰顯出來的超驗心,必然會
逍遙乘化、自由自在
。
從傳統(tǒng)武術(shù)的角度看,老子說“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
,其實已經(jīng)闡述了方法與智慧的關系
。就傳統(tǒng)武術(shù)而言有,乃是武術(shù)運動實踐的具體方法與手段
;無即道
,既可指產(chǎn)生這些具體的方法與手段的人的超驗心,也可指無化的過程以及無化以后的無的境界
。把老子的這句話放到傳統(tǒng)武術(shù)的語境中
,是在說明這樣一個道理:
最為理想的武術(shù)實踐方法,根源于習武者本就潛在的超驗心;而習武者的這種超驗心的顯現(xiàn)與發(fā)揮,需要習武者通過無化而達到無任何造作私為的精神境界。
筆者認為,在傳統(tǒng)武術(shù)的語境下詮釋老子,并不是對老子的臆解。對道的關注與重視是老子思想的鮮明特色。然而,對道的關注與重視,并不意味著老子完全摒棄了具體的方法與手段。實際上
,老子在強調(diào)道的根源性質(zhì)的同時,不但明確強調(diào)“反者道之動
,弱者道之用”而把反動與弱用作為處理經(jīng)驗事物的方法論
,甚至還就不同領域的不同問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具體方法。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fā)狂
,難得之貨令人妨
。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
”“絕圣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
,民復孝慈;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
。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
,故有功;不自矜
,故長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
,荊棘生焉;大軍之后
,必有兇年
。善,有果而己
,不敢以取強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果而勿驕
,果而不得己,是謂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
,是謂不道;不道早己
。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
,自勝者強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不失其所者久
,死而不亡者壽。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
,是以難治
。民之輕死,以其上生生之厚,是以輕死
。
” 無論是方法論,還是相對具體的手段,都意味著老子對方法的關注
。雖然老子并不提倡就方法談方法,反對造作私為的方法
,但是,老子十分清楚無論多么高深的道
,最終都要落實到具體的事物上而以具體的方法來表現(xiàn)的
。
“天下有始 ,以為天下母
。既得其母
,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沒身不殆。塞其兌
,閉其門
,終身不勤
。開其兌
,濟其事
,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用其光,復歸其明
,無遺身殃
,是謂襲常
。
”
于此老子的守母以存子的思想邏輯己非常明確。天下萬物的產(chǎn)生都有根源
,自然處理各種具體事物的方法
,也都有個智慧的根源。作為一種超驗心
,道是理想的經(jīng)驗方法的根源,是萬法之母
。當潛在于我們的道得以顯現(xiàn)時
,應對經(jīng)驗事物的方法必然是不需考慮的。既然我們知道理想的方法皆是道的表現(xiàn)何不在現(xiàn)實的萬法中通過對現(xiàn)實方法的超越來彰顯超驗的道呢
?

抱神以靜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 。知其榮
,守其辱
,為天下谷;為天下谷
,常德乃足,復歸于樸
。
”在老子看來,人生最明智之舉 ,是向道的復歸
,也就是所謂的復歸于嬰兒、無極
、樸
。
“老子之道,本是由遮而顯,故況之曰‘無’。他首先見到人間之大弊在有為,在造作,在干涉、在騷擾,在亂出主意,在亂動手腳,故有適,有莫,有主,有宰,故虛妄谿結(jié),觸途成滯。其弊總在‘有為’,‘有執(zhí)’也?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世献又^圣棄智
,絕仁棄義’,實非否定圣智仁義.而乃籍‘守母以存子’之方式
,‘反其形’以存子也?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献铀f之無、一
、自然
、玄、遠
、深
、微、諸形式特性,固亦皆可有之
,然皆成為仁體屬性
,或踐仁至至之境界之屬性
。固不只是沖虛之無為本
,而是以仁體為本也。此是自實體上肯定仁智
,固不只是作用之保存也。此是儒道之本質(zhì)的差異
?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蹦沧谌壬杂忻黠@的儒家情懷
,但也真正把握住了老子思想的邏輯與精髓
。
從現(xiàn)代的角度看,對于人類經(jīng)驗的真實可靠性,老子是持懷疑態(tài)度的。在老子那里,超驗心的彰顯具有十分主要的地位,而彰顯超驗心,最終還是為了保證人們在生活實踐中的各種具體方法的適宜性與合理性。從理論上講,生活實踐的方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然而,最適宜最合理的方式只能有一個,即是合于道、合于自然
。老子對道的強調(diào)
,并不意味著老子十分鄙視現(xiàn)實的生活實踐,更不意味著老子追求的是一種逃離現(xiàn)實世界的精神超越
。事實上“它欲解決的是超越和現(xiàn)實的關系問題?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崩献铀p視的“為學”
,是那種只重概念思維而忽視道的存在的“為學’。學習合道的知識
,在對知識的學習與掌握中體悟道的存在,雖然也是一種“為學”
,但老子并不反對。
以適宜的方式正確地處理好生活實踐中的各種具體事物,通過長期的生活實踐的磨練逐漸去除一切人為造作
,超越有限的方法而體悟到道的存在
,乃是老子處理道與有
、無相互關系的基本模式。也就是說重視道與無未必一定要排除對基本技術(shù)的學習
,只是強調(diào)在實踐中要不斷地超越這些技術(shù),而不把這些技術(shù)作為僵化的模式
。
“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
;方今之時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
,批大郤
,導大窾,因其固然
;枝經(jīng)肯綮之未嘗微礙,而況大軱各乎
!
”庖丁所好者.是道而不是技;然而
,其所好的
道,卻是在對技(即術(shù))的反復實踐中獲得的
。其實,得道以后的庖丁解牛所運用的道
,也是一種技
,只不過不是那些庸俗的屠夫們所理解的技而己
。真正的技(即術(shù))
,乃是在道得以彰顯之后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的直覺能力
,然而,這種直覺能力的獲得卻也是要經(jīng)過“無非全?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未嘗見全?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谋厝浑A段的
。
傳統(tǒng)武術(shù)家們所追求的,何嘗不是這種能夠充分把握武術(shù)實踐的道呢 ?而傳統(tǒng)武術(shù)家們對這種道的獲得又何嘗不是要經(jīng)由一個艱苦的術(shù)的磨練過程呢?現(xiàn)在看來
,
游刃有余的道的彰顯 ,實質(zhì)是經(jīng)過了一個從感觸直覺到經(jīng)驗直覺
,然后再由經(jīng)驗直覺到智慧直覺的熟練與超越的過程
。
以道為終極目標倡導“復歸于無極”,強調(diào)在具體的生活實踐中超越方法的局限而體悟道的存在,乃是一種內(nèi)向性的思維方式
。這正是中國古代思維的基本特色。這種獨特的“
術(shù)以道為目標”而不是“術(shù)以知識理論為依據(jù)”的思想邏輯,體現(xiàn)了中國古人對技術(shù)訓練與實踐技巧的藝術(shù)追求。
“術(shù)以道為目標”,是一個內(nèi)向的、體悟的
、經(jīng)驗的
、超越的過程;而“術(shù)以知識理論為原則”
,則是一個外向的、分析的
、理性的、邏輯的過程
。正是因此
,中國古人在處理各種具體事物的過程中,雖也不乏對方法手段的關注
,卻很少會對這些具體方法進行靜態(tài)的、邏輯的
、對象化的研充
,因為
,在中國古人的心目中
,
最合理的方法手段絕不是抽象與分析的結(jié)果,而只有“復歸于無極” ,復歸于道,才進入了方法手段的最高境界
。
老子道家對道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是為了獲得圓滿生活的智慧 ,是為了圓滿地處理好生活實踐中的各種問題
;同時老子道家對道的彰顯,又堅持要在具體的實踐中得以完成
。
道是最圓滿的術(shù) ,道又是在對術(shù)的修煉中得以彰顯的。無論是專門的“致虛極
,守靜篤”的“為道”修煉,還是日常的生活實踐中以“道進乎技”為指導的“為術(shù)”
,從形式上看 ,其實都是“為術(shù)”
,卻又都以“為道”為終極目標
。

人的一切行為 ,都需要以一定的方法方式來展開
;然而
,人的最明智的修養(yǎng),都應該以道為核心來展開
。無論是運用特殊的手段來直接開發(fā)人的超驗心,挖掘人的內(nèi)在潛能
,還是通過學習先賢總結(jié)的智慧方法
,用智慧的方法來處理具體事物
,在處理具體事物的實踐中逐漸地體悟道的存在,都應該是向無極之道的復歸
。
武術(shù),是一種非常具體的操作活動;自然,對所有武術(shù)活動的操作來說,必然要以術(shù)的形式來完成。然而,常令人費解的是,雖然武術(shù)活動的操作非常明顯地是一種術(shù),但是,傳統(tǒng)武術(shù)家們卻?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诳诼暵暤貜娬{(diào),傳統(tǒng)武術(shù)所追求的
,乃是道而不是術(shù)
。
“復歸于無極”,這一源自道家的思想觀念,是傳統(tǒng)武術(shù)家們堅信不疑的。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難道武術(shù)的訓練過程 ,可以拋開具體的技術(shù)方法而去追求那個虛無縹緲的道嗎?道家那些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拳手的精湛技術(shù)是與技術(shù)訓練沒有關系的修道使然嗎
?無論查閱文獻資料,還是考察運動實踐我們都不
會發(fā)現(xiàn)過任何一種有道而無術(shù)的拳種 。
其實,在傳統(tǒng)武術(shù)中 ,“復歸于無極”
,只是強調(diào)道是武術(shù)訓練的終極目標,而并不是對武術(shù)之術(shù)的排斥
。
“復歸于無極”是一個從有為到無為的損之又損的心理甚至是超心理訓練過程。這是一種對心理訓練目標的終極設置;自然,在實踐操作中,這必然是一種對習武者的極端要求。它輕視與反對人們在運用術(shù)時的一切人為造作。在訓練心理上的終極追求,使傳統(tǒng)武術(shù)多少有了一點宗教的魅力。
傳統(tǒng)武術(shù)對術(shù)的根源與目標的高度重視并不排除其對術(shù)的深入關注?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蛟S
,正是因為傳統(tǒng)武術(shù)對術(shù)的根源與目標的高度重視才使其對每一具體的
、局部的術(shù)的深入研究成為可能。當然
,這種對術(shù)的深入研究,是體悟性的、實踐性的
,而不是分析性的、邏輯性的
。
對道的重視是為了真正確保術(shù)的適宜性與合理性;而對術(shù)的深入研究是為了向道的接近。
“復歸于無極”,是傳統(tǒng)武術(shù)家們的理想歸屬。因此,雖然傳統(tǒng)武術(shù)家們在具體實踐中對各種技戰(zhàn)術(shù)與武德規(guī)范等的學習與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是傳統(tǒng)武術(shù)家們卻從不敢忘記“為術(shù)以悟道為最終目的”,力爭在“為術(shù)”中達到無的境界而體悟道的智慧
。“形意拳之道
,是先將拳術(shù)己成之著法玩,而求之而有得之于心焉
,或吾胸中有千萬法可也
,或吾胸中渾渾淪淪無一著法亦可也
。無一法是一氣之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