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宣說的神秘:佛教禪法與道教丹法之比較研究
魏小?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ㄈA東師范大學(xué)哲學(xué)系)
|
修道所追求的“此世成就”,很大程度上正是要通過轉(zhuǎn)化肉身來實現(xiàn)。既然丹道并不以身體“不凈”,它對治欲望的方式就不是制伏,而是利用正常的凝神調(diào)息等修行活動引導(dǎo)欲望自行消解……
|
宋元以后的道者汲汲于援佛入道,大倡仙佛同宗、佛道一家之說 。但是在歷史上,佛教在中國最初是被視為道術(shù)之一種來理解和接納的
,“其流行之教理行為
,與當(dāng)時中國黃老方技相通”。
誠然 ,佛教與道教在中國的土地上同生共長近兩千年
,彼此間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在所難免
,但若要貿(mào)然宣稱佛
、道從本質(zhì)上說即全然無別
,則尚需深入精微的分析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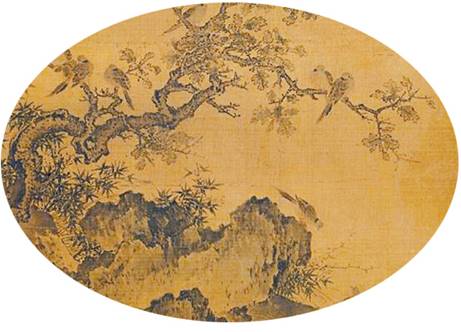
“立教者,圣人救世愍物之心也。”《云笈七簽·卷三》不論何種宗教,開宗立派總緣悲憫,但先覺者選擇以何種方式傳教立說、救護世人,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dāng)時的社會歷史情境及其自身的文化土壤。印度的冥修傳統(tǒng)根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和上古傳說可以上溯到史前的印度河文明時期,而中國的修仙傳統(tǒng)依據(jù)出土器物和先秦文獻同樣可以溯源到華夏文明發(fā)端處的黃帝時代乃至伏羲時代。
以后,印度河的宗教文明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遭蠻橫破壞,崇尚力量注重祭祀的婆羅門教遂超越冥修成為主流。中國的神仙信仰卻從未間斷,后世道教對各種地方性小傳統(tǒng)一視同仁兼容并蓄也使得它在中原文化圈內(nèi)幾乎無往而不勝。也就是說,印度和中國的上古文化均帶有強烈的超凡入圣訴求,這在佛教和道教便分別表現(xiàn)為對冥思禪定和內(nèi)煉丹法的格外注重,并將此視為通向解脫的根本道路(有別于一神教的依他力救贖);但印度文明和華夏文明分別經(jīng)歷了不同的觀念融合的歷史,印度佛教和中國道教各自所處的時代背景所面臨的救度對象更多有不同,因而在教法教義上會表現(xiàn)出這樣那樣的差異。

在對早期佛道經(jīng)典的解讀過程中,需時刻分辨哪些是“方便說法”、哪些是“了義說法”————此時此地一方信眾是以如此這般的方式陷入無明,因而佛陀、天師要這樣那樣地宣講施教;后世諸多義理問題的出現(xiàn)更多是具體歷史語境下的產(chǎn)物,而非由原始教義自身所生發(fā)。那么,哪些教法是超越歷史、超越時空,可以一直通往永恒,而只有通過它才有可能對佛法與道法之本性異同作出終極評判
?最可信者或當(dāng)首推宗教踐行和宗教體驗層面的佛教禪法與道教丹法。(
備注:本文所說的“禪法”大體指“進入禪定之實際方法”,與梵文“禪”
、“禪那”的“靜思慮”初義已不盡相同
,而現(xiàn)當(dāng)代佛教學(xué)術(shù)論著中基本均在此種意義上使用“禪法”一詞。道教之“丹法”有體內(nèi)凝煉的“
內(nèi)丹”和爐火燒煉金石以供服食的“外丹”兩種,本文的“丹法”僅涉及
內(nèi)丹,且廣義上包含其他各時期的內(nèi)在精神一致的煉養(yǎng)方法。
)
同樣作為 “東方神秘主義”的一部分,禪法與丹法的形似和神似是顯而易見的。但禪法與丹法究竟在何種意義上“相通”,這種“相通”是出于同一宗教實踐的不同表達,還是性質(zhì)迥異的兩種實踐行為偶然性地表現(xiàn)出了令人訝異的相似,則需從實修方法、次第、境界等方面詳加考察。
日益熏染了“中國特色”的中土禪法
佛學(xué)對于中土是舶來之物,因而一個時期內(nèi)中土所流行的禪法品類既與當(dāng)時佛經(jīng)譯介者的眼界和傳承息息相關(guān),同時也取決于本土文化對這些翻譯文本的思想、方法的認同程度和吸納偏好。于是,中土禪法的發(fā)展就呈現(xiàn)出與印度不同的脈絡(luò)。

中國最早一批翻譯家所傳譯的經(jīng)典里已有重視禪定傳統(tǒng)的“禪數(shù)學(xué)”。自姚秦東晉時期羅什、覺賢來中國傳授大乘禪法之后,南北各地習(xí)禪風(fēng)氣一度十分興盛。進入南北朝,南方佛學(xué)轉(zhuǎn)向玄談,只北方佛學(xué)仍舊偏重實踐。至南北朝后期,北方逢周滅佛,南方經(jīng)論講習(xí)之風(fēng)日盛而禪修之風(fēng)益衰,習(xí)禪真有所得者越來越少,乃有開創(chuàng)本土禪法之先的天臺止觀學(xué)說出世。
據(jù)湯用彤先生所見,漢晉時期中土流行的禪法大體有:念安般,即觀出入息(安為入息
,般為出息),代表經(jīng)典如安世高所譯《安般守意經(jīng)》不凈觀
,羅什所譯的三部禪經(jīng)專輯《坐禪三昧經(jīng)》《禪法要解》《禪秘要法經(jīng)》
,覺賢譯的《達磨多羅禪經(jīng)》均倡言此門;念佛
,即觀想十方諸佛悉在前立或觀想諸佛國土
,以支讖所譯的《般舟三昧經(jīng)》為最初之經(jīng)典
。
隋唐有宗派之興起,嗣后禪法亦可以宗派相別,而尤以天臺
、禪宗、
凈土和真言(密宗)為大宗。

相較于其他宗派的熱衷玄談,天臺一系亟言禪定之重要,所倡導(dǎo)的“定慧雙修”也以由禪生慧為主旨
。其禪法以智姸的《摩訶止觀》為代表作
,義理承襲中觀而別有創(chuàng)見,定觀上則以中觀的空
、假
、中三種實相為對象,乃義理與實踐相契的典范
。天臺對其他諸宗的批判多出于義理上的歧見
,實修方法則吸收了諸家之長,包括唱誦佛名號(常坐三昧)
、觀想佛形象(常行三昧)
、誦經(jīng)(半行半坐三昧)之類,
天臺尤其吸納了道家煉養(yǎng)體系,其創(chuàng)始人智顗大師的著作里面
,記載有大量的道教修養(yǎng)法門。
在證果上,天臺所證之“法華三昧”,非為次第禪門,而為圓頓一乘法門:“一心一學(xué),眾果普備;一時具足
,非次第入
。”慧思《法華經(jīng)安樂行義》
禪宗本出于戒律極嚴的楞伽師,其禪法“專唯念慧
,不在話言”。盡管據(jù)僧傳記載達摩所傳入道之途有“二入”
、“四行”之說
,但具體禪法如何已不可確知。到唐代
,東山法門又教人“莫讀經(jīng)
,莫共人語”地“閉門坐”(敦煌卷子《傳法寶記》)
,禪法則是從“專心一佛,稱念名字”到“念念相續(xù)
,于念中見一切佛”再到“忽然澄寂
,更無緣念”
,進入“一行三昧”的境界
。到南北分宗時,北方神秀一系所傳的是“凝心入定
,住心看凈
,起心外照,攝心內(nèi)證”的“漸法”南方慧能
、神會一系則以一念般若即可成佛
,因而大倡“直了見性”的“頓法”。所崇奉的經(jīng)典也逐漸從《楞伽經(jīng)》轉(zhuǎn)入《金剛經(jīng)》和《大乘起信論》
。到唐末暢行天下的禪宗那里
,“禪”的意義被擴大了,不一定要靜坐斂心
,只要心不散
,平常的行住坐臥都可以和禪打成一片,因而“定無所入”成為這一系禪法的主流
。

凈土信仰,在兩晉時期即已流傳,且有如道安
、玄奘這類聲名顯赫之高僧崇奉
,勢力漸著,蔚為大宗
。念佛本為一種大乘禪法中常見的修持方法
,其本意乃在觀想、憶念諸佛或佛土以入禪定
,雖不排斥“執(zhí)持名號”
,但絕非只宣唱佛號而不修禪定的口頭念誦。后世民間教眾全依凈土宗的“三經(jīng)一論”而信奉贊嘆佛名有不可思議之威力
,大約亦與本土古已有之的對咒語的信念以及流行一度的密宗對真言之崇奉不無關(guān)系
。
然凈土所倡,終究為期冀借他力獲得往生 ,且極樂凈土的性質(zhì)
、往生的性質(zhì)、往生極樂眾生之生死的性質(zhì)等問題,與原始教義頗有參差
,為現(xiàn)代學(xué)者所詬病便不足為怪了
。
印度大乘佛教后期(7世紀(jì)以后)向密教的轉(zhuǎn)變,一般被認為是傳教訴求與社會變遷相妥協(xié)的結(jié)果。密宗對儀式
、祭祀的考究,對結(jié)印
、咒語的依賴
,顯然出于對印度教的效仿。但這些因素實際上在大乘佛教早期即已存在
,從三四世紀(jì)的漢譯佛經(jīng)即可看出端倪
。但中土專修真言密語風(fēng)潮的興起實際發(fā)生在印度的密教化轉(zhuǎn)型之后,與三位印度密宗大師善無畏
、金剛智和不空金剛?cè)胩苽鹘讨苯酉嚓P(guān)
。宋代曾一度沉寂,再興就已是為元
、清兩外族統(tǒng)治者的喇嘛教所推崇的關(guān)系
。密教注重方法而較少高深教義的討論,禪法上以
手印和咒語結(jié)合意密觀想,尤為獨到
。一般認為,密宗對中國思想并沒有產(chǎn)生很大影響
,但唐代以降
,持誦《心經(jīng)》《大悲咒》《楞嚴咒》等經(jīng)咒在禪修者當(dāng)中日益常見,元明以后更成為僧人日常功課的一部分
,對經(jīng)咒之聲音力量的推重以及對凈土佛號的執(zhí)著信念未始不有密宗真言信念的間接影響
。

在上述傳布較廣的禪法之外,各時期尚流傳許多“觀法”。如早期有觀“五蘊成敗變化”之法,為安世高、竺法護等譯經(jīng)家所看重 ,曾重點譯介頗具代表性的《修行道地經(jīng)》
;羅什編譯的《坐禪三昧經(jīng)》中對治嗔恚的法門為“觀四維上下各方眾生”
,對治愚癡則“觀十二緣起”《成實論》中亦有“無常想
、苦想、無我想
、食厭想
、一切世間不可樂想、不凈想
、死想
、斷想
、離想、滅想”等“十想”觀法
。隋唐諸宗派
,天臺宗的“正修止觀”包括觀陰界入、觀煩惱等十乘觀法
;三論宗有以“八不”入手的“中觀”法門
;慈恩宗教人觀“諸法唯識”華嚴宗則觀“十玄無礙”和“六相圓融”。這些“觀法”既是實修入禪定之真實法門
,亦可代表各派學(xué)說之特點
,但“觀法”對義理理解能力要求偏高,且多涉精細之分辨
,與中國本土的思維方式不甚相合
,在禪修者中間遠不如各種方便法門深入人心。
總體上 ,
如果說漢晉禪法注重溯流窮源(羅什就曾遭到同代人的詬病,以其學(xué)無師承),尚與原始佛教相去未遠,隋唐以后的禪法已基本脫離了對印度佛教的心理依賴,至少從形式上日益與原始佛教分道揚鑣:天臺止觀涉及多種三昧,仍以靜慮之“坐禪”為主,尚對印度禪法盡可能有所保留;到慧能、神會所傳之禪宗,雖云行多種方便,主調(diào)卻是“行亦能禪坐亦禪”的“日用是道”,其所力倡之“頓法”,既對禪修者個人根基有特殊之要求,便與印度佛教頗有距離;至于修凈土者心系彌陀凈土,而主修唱誦此佛名號之法門,以及修密宗者在瑜伽、三密、灌頂?shù)戎T多禪修行為中間尤重真言密語,均與原始佛教大異其趣。
宋元以降各派禪法更加不重傳承,而趨向采取禪密、禪凈或凈密等多重法門兼修的修學(xué)方式,愈發(fā)顯示出鮮明的“中國特色”。
道教丹法從守一到存思到內(nèi)丹的歷史變遷
道教內(nèi)修的“丹法”,常被認為是唐末五代以后的新興事物,其實,文獻學(xué)的“內(nèi)丹”一詞雖然出現(xiàn)較遲,但凝神煉養(yǎng)事實上是一種由來已久的修身手段。先秦時期即已廣泛流行的《行氣玉佩銘》及上古傳說中廣成子與黃帝之間的仙道授受,在在說明了修仙傳統(tǒng)幾乎與華夏文明自身的歷史一樣久遠。
縱觀丹道發(fā)展歷史 ,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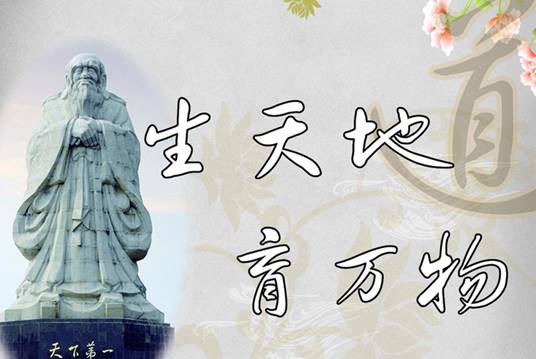
第一階段,先秦道家 、醫(yī)家
、神仙家的抱樸守一、導(dǎo)引行氣
、採氣餐霞
。
作為道教宗教體驗內(nèi)核的仙道煉養(yǎng),可以一直溯源到華夏文明的起源處。先秦文獻里所記述黃帝受教于廣成子的“無視無聽,抱神以靜”(《莊子·在宥》),《道德經(jīng)》里的“載營魄抱一”、“致虛極,守靜篤”,《莊子》中的“聽息”、“心齋”、“坐忘”,即晚近內(nèi)丹術(shù)所說的一種“清凈修法”,與“陰陽補法”實質(zhì)并無不同——亦有“火侯”,不過“清心寡欲,主靜內(nèi)觀,使真氣運行不息”而已;亦有“進退升降”,不過以“真水常升,真火常降”而已;亦有“沐浴”,不過“懲忿窒欲,滌慮洗心,令太和在抱”而已;亦有“得藥成丹”,不過“以神為父,以炁為母,兩兩扭結(jié)一團,融通無間,生出天地生我之初一點真靈?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笨傊?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即自身龍虎交媾意義上逐層修煉
;一種名曰“清凈而修”,如同天道運行
,自然而然
,令“清空一氣,浩浩蕩蕩
,自然一呼一吸上下往來”
。見黃元吉《道德經(jīng)講義》八十一章)
 成一體,始悟先天玄中玄
成一體,始悟先天玄中玄。
《楚辭》等文獻中述及的采氣、餐霞一類的養(yǎng)生功夫,為后世存思法門的前身
。
東漢的《黃庭》、《玉歷》諸經(jīng),《太平經(jīng)》里所說的“五藏精神”乃至南北朝上清一系系統(tǒng)的存思
、存神等方法
,構(gòu)成了漢魏六朝乃至隋唐道教內(nèi)煉工夫的主流,可視為丹道發(fā)展的第二階段
。
無論是存思紫氣、存想神名,還是存想日月星辰,或餐六氣、含朝霞,均旨在通過意念引導(dǎo)調(diào)動自身真氣與天地之氣的先天關(guān)聯(lián)。在進入杳冥的狀態(tài)下,借存思存神激發(fā)內(nèi)丹術(shù)所說的“自在性光”,促使人的精神氣質(zhì)和肉身體質(zhì)逐步凈化,直至發(fā)生從凡俗肉身到成仙成圣的飛躍。也就是說,存思法與內(nèi)丹術(shù)的凝神調(diào)息洗心滌慮,起始手段有所不同,但同樣要發(fā)動先天真陽之氣,通過真氣的升降流轉(zhuǎn)運化精氣神,育養(yǎng)金丹仙胎。存思法門背后的義理依據(jù)和入道以后的修行路線與內(nèi)丹術(shù)完全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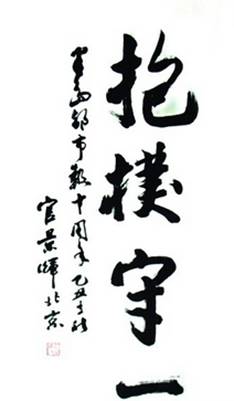 守一。
守一。
第三階段即唐末五代以來發(fā)展起來的內(nèi)丹術(shù)。
宋代以后內(nèi)丹雖亦形成了不同流派,不同丹經(jīng)所傳起始方法亦有小別,但清修丹法均遵循筑基———得藥———溫養(yǎng)———出神這一循序漸進
、逐層修煉的路線
。內(nèi)丹逐漸形成了一套自成體系的完整術(shù)語結(jié)構(gòu),如以身為爐鼎
,心為神室
,津為華池;心中真陰為離
,內(nèi)含一點真陰之精
,被稱為青龍、姹女
、甲木
、水銀、真汞
、金烏
;腎中真陽為坎,內(nèi)含一點真陽之炁
,則屬白虎
、嬰兒、庚金
、朱砂
、真鉛、玉兔
;心腎之間即中央戊己
,為黃婆;采煉即以先天真氣為藥物
,以真息為神火
,元神斡運其間,在已身中運煉
,將其聚凝成為黍米之珠
,即內(nèi)丹
;進一步結(jié)胎成嬰,道教即以之為“法身”
,再久久涵養(yǎng)
,成就“陽神”,即為不死真仙
。修道至內(nèi)丹術(shù)這里似乎變得輕而易舉———明了這一套術(shù)語的象征意義
,依照丹經(jīng)指引按圖索驥即可
。
抱樸守一、存思存神、內(nèi)丹技術(shù)
,分別代表了丹道早
、中、晚三個階段的主流功法
。這三種功法盡管具體修行方式有別
,但義理基礎(chǔ)和作用機制并無不同———肉身具有神奇根性,凡人受生乃“法九天之氣
,氣滿神具
,便于胞囊之內(nèi),而自識其宿命
,知有本根
,轉(zhuǎn)輪因緣九天之劫,化成其身”(《上清九丹上化胎精中記經(jīng)》)
。
人的肉身與天地之間存在著先天的聯(lián)系和同一性,于是各種修道方式均旨在“歸根復(fù)命”,重新建立起“受生于天魂
,結(jié)成于元靈”的天人關(guān)聯(lián)
,找回被遺落的自己,即那個真正的
、神奇的“本來人”
。(《太丹隱書》)
某種修仙方式的流行,雖不致與其所處的人文環(huán)境嚴格對應(yīng),但亦可捕捉到顯然的關(guān)聯(lián)
。如先秦民風(fēng)淳厚質(zhì)樸,人心清凈
,修道之方法亦貌似疏簡而其實古拙
;六朝隋唐崇尚華麗風(fēng)雅,上清一系內(nèi)志玄遠
、文風(fēng)清麗的存思法門遂盛行不衰
;宋代以后人心不古
、道德沒落,丹法即趨于平實明晰但亦多勉強造作
。因而守一
、存思、內(nèi)丹這三種修真技術(shù)
,既可視為互不相同但為各時代最具代表性之修道方法
,亦不妨看作同一丹法的不同形態(tài),在表達方式上存在著鮮明的遞進關(guān)系
。
禪法與丹法的修法 、次第、境界和修行原則
對中土所傳的佛教禪法和道教丹法之脈絡(luò)的簡單梳理 ,或可有助于我們在禪法與丹法的比較中時刻關(guān)照到某一法門所流傳
、盛行的歷史脈絡(luò)和文化語境,以避免使這一比較流于泛泛
。
佛 、道兩家在歷史上經(jīng)受了多次兩敗俱傷的論戰(zhàn)、斗法之后
,南宋金元以降終于真正了走了“融合”
、“歸一”的歷程。諸家對“三教歸一”的論說各具特色
,而道門中人最為傾向于援引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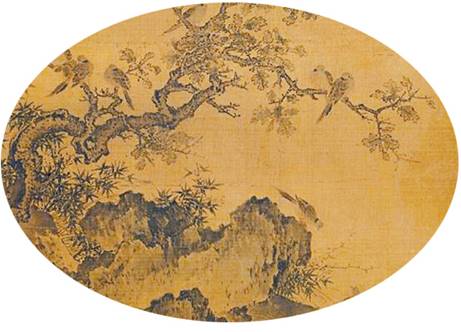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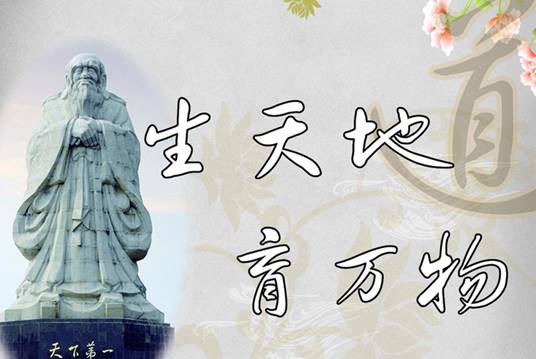
 成一體,始悟先天玄中玄
成一體,始悟先天玄中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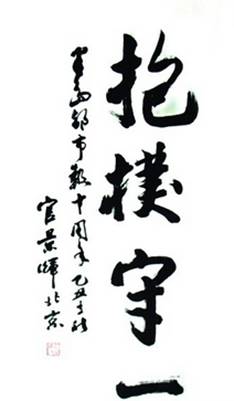 守一。
守一。